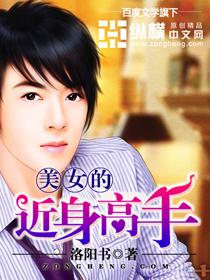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网恋对象是我哥林晓晓免费阅读 > 第59页(第1页)
第59页(第1页)
席妙妙步履轻快地走到楼下,行李都不要了,横竖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回s市再买就是。她走至人烟罕至的小巷里,扬着唇角,将玉佩从裤袋里拿出来,握在手心,内心的声音欢快得像只小鸟。“封殊,快来接我呀。”她捂住脸,不合时宜地高兴着。就像积压了很多很沉的包袱,负重前行多年,现在她将包袱摔在地上,高呼一声‘爷不干了!’身心松快,真怕走着走着人都要飞起来。她一眨眼,就掉进一个怀抱:“……哥们,我们打个商量好不,下次你出现,给点预告。”“吓到你了?”“有点,不过感觉不坏,挺好的,”席妙妙转身,伸手捏了捏他的脸:“我的盖世英雄,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接我。”封殊思索片刻:“炼仙袍可以变色,但七彩祥云我要跟天帝借一借,下次你跟温语出去玩,我穿这一套来接你。”“……”她想抽自己嘴巴了,咋就这么能乱说话呢?“但是,你不觉得这更加吓人吗?我穿着金光灿烂的衣袍在天上飞,踩着七色的祥云……”神中杀马特,非他莫属。席妙妙被想象出来的场景逗笑了,她唔的一声:“好吧,你说得有道理,还是正正常常来接我的好,有种男朋友来接送的感觉。”“我就是你男朋友。”“好好好,男朋友,”她牵起他的手,笑着在他手背上吻了一下:“走吧男朋友,我们买票一起回家,过中秋去,你吃过月饼吗?对了,天上月亮,真的有嫦娥吗?”“没有,有。”“什么样子的?漂亮吗?”“……我不认识她,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仙女。”神中资深家里蹲如是说。想到他的情况,席妙妙体谅地没追问下去,转移说起了别的话题:“我们回家一起吃月饼,传统馅的好吃,冰皮的可以当甜点,我每年在家里过完中秋之后,回来s市,都会跟温女神一起,把收到的月饼开来吃,说好一起节后胖十斤,她却偷偷健了身,嗨呀想起都扎心!”尽说些无关要紧的废话。一句句废话积累下来,就是两个人的日常,最好的爱人,可以说一辈子废话也不会腻。“你很轻,多吃点。”“我很轻?大兄弟你的良心不会疼吗?偷偷跟你说,我105斤了。”“我一根手指能把你抬起来。”席妙妙语塞,说不过他了。跟这种无底线宠溺的男人在一起,很容易会对体重美丑的标准感到麻木,最亲近信任的人天天对着你真心实意地说,你很美很瘦,渐渐的,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了,连饭都多吃了两碗。要保持体重,就得保持警惕啊!“你狡辩,我吃成两百斤的胖子也好看吗?”“好看,我喜欢。”听,这神说的都是什么话,不说人话的。席妙妙听得痛心疾首,笑容却越扬越高,笑得嘴角都疼了,她只能用另一只手捂住下半张脸,活像赚了一笔大的小偷,想将喜悦藏起来,可又怎么藏得住呢?来来往往的人,瞥二人一眼,都知道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起回家,过中秋。***回到s市的家后,席妙妙迫不及待拨通了温女神的电话。“女神,今年中秋我在s市过!”“哈?你爹妈不活撕了你?你不是跟封殊一起回老家了吗?之前他还找我家狗支招呢?”背后传来抗议:“我是龙,不是狗!”温女神飞快地用方言驳了回去:“龙生九(狗)子,你就是那只狗子。”“用广东话欺负人!”席妙妙被这对活宝逗笑了,两人在电话里一同取笑伏云君,洋溢着快活的空气:“好了,说正经的,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不是才回老家一晚,发生什么事了吗?跟他们吵架了?”不愧是温女神,反应得真快。她将事情原由一说──换了别人,还须忐忑会不会劝自己不要冲动,说得太狠,可是跟温女神,她一点也不担心。果然,温语一拍大腿:“说得好,早该撕了!”两人知根知底,她知道妙妙的家庭关系如何,也知道老家的人是怎么编排她们两个离家出走,到大城市闯荡的异类。男娃出去大城市是男儿志在四方有出息,而她俩?无论赚了多少钱,钱也是来历不明的,是嫁不出去的坏例子,不安於室。温语早就跟家里决裂了,只把一直关爱自己的外婆接到s市来照顾,前年外婆病逝后,她更是完全断了联系,哪个亲戚来s市玩想蹭她的地儿住都没门。“我也这么觉得,有些话,早该说开来了,不该心存希望的。”不摊牌,就永远不知道,对方有多不爱你。席妙妙笑着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爱我啊。”电话里,她低低笑了一声:“别难过,我爱你。”“qaq!”背后被封殊拥住,他吻她耳背,恐落於人后:“我也爱你。”席妙妙捂脸失笑,跟温语在电话里,痛痛快快地忆苦思甜,将陈年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说。这个倾诉对象,不会笑她心眼小,一点破事记上许多年,她完全理解接受她的伤痛,互舐伤口,说到痛处,竟是不约而同的大笑出声,几乎要笑出眼泪。“气死我了,居然说我骚,我又不勾引她!”“你一直不化妆,第一次听这种话吧!我从十六岁听到现在,没办法,我素颜嘴也红得跟擦了口红似的,”人比人气死人:“那时有个亲戚不信,捏着我的嘴一顿捏,死不松手想整哭我……你还记得我怎么做来着?”“我当然记得,整个镇上都知道了,你把人手指都咬流血了,好像一直少了块肉?”谈论起这些大逆不道的‘丰功伟业’,席妙妙与有荣焉,只觉自己浪费了好多次撕回来的机会。这点,她确实远不如她。现在温语混出来了,光鲜亮丽地活着,可是行事依旧有着不疯魔不成活的狠劲,也是够凶,才能在那环境里维持住最底限的尊严──就像《变形计》里凶恶的农村孩子,他不想有素质么?环境迫人,嗓门大才能立住脚根,凶归凶,本质是好的。封殊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二人聊得兴高采烈,他亦听得入神。那些他不曾參与其中的过往,他都很感兴趣,想知道妙妙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听她说得高兴,因为她跟家里人吵架而高悬着的心也稳了下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纠纷,也不知道有多难过……可能,穷其一生,也不会了解这凡人构成的家庭情感了。只是察觉到了妙妙低落的情绪与眼泪,担心她的情况。他用脑袋蹭了蹭她的颈窝,听她抖豆豆似的语速,听得很愉悦。温语话锋一转,“说句实话,妙妙,你跟家里说开来了,心里感觉怎么样?”“……我,”面对这个问题,席妙妙迟疑地顿住,她不自觉地用手摸了摸胸膛。只摸到了起伏微小的胸脯,以及隔着骨胳皮层,脉脉跳动着的心脏。她见过心室图,知道心脏的构造,那不是什么诗意浪漫的模样,却总和感情扣上关系,负责分析的明明是大脑,疼起来,却是输血的心脏在疼。现在,它好像不疼。“我以为我会很伤心难过,但开口的刹那,就感觉,啊,不过如此嘛,那些很难说出口的话,原来只是碰碰嘴皮子,说得挺流畅的,”她眨了眨眼睛,心脏跳得很快,很快,快得开始疼了:“我记起了拖拖,它不是‘老家里养过的一条狗’,是跟我感情很好很好的朋友,它爱我,”“然后,回来之后我发现,你爱我,封殊也很爱我,”爱这么沉重认真的一个字,彷佛该到人到将死之时,才能用一句‘我……你’郑重说出来,席妙妙这时却一气儿说了三个爱字,肯定了三份爱,她笑出眼泪,深呼吸:“太高兴了,我何德何能啊,被爱着的感觉超级好,我早该面对的,差点就忘了拖拖也爱着我,嗯,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