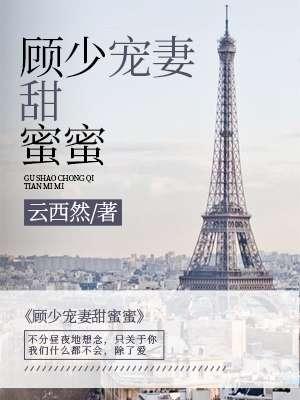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的团长我的团死了几个演员 > 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1页)
那小子坐在我身边,笑得直咳嗽,&ldo;拉弦了,这回我拉弦了。&rdo;
我回头看了看我们曾血战的山顶,硝烟在散,站的,躺的,坐的,像我一样刚放弃追击的,还有一些气喘吁吁一直在爬山刚爬入我们中间的,像阿译豆饼郝兽医这一拔子‐‐那一批刚进入就有好多栽倒的,趴在地上呕吐。死啦死啦把他们踢起来,而迷龙把一面日本军旗拔下来扔了。
我呆呆看着他们。
与死啦死啦为伍就得预备好在谎言中生活‐‐被我们从山顶撞下去的日军足一百多人,两个加强小队,斥候绝没有这么大规模‐‐他们甚至已经在峰顶插上了军旗。
没死的人傻呵呵地乐,十五分钟,我们把占绝对制高点的敌军赶回林里吃草,干掉他们三分之二。我们冲向一条巨大的恶犬,龇出我们以为早已经退化没了的獠牙,吼着。我咬死你。
死啦死啦在交叉挥动着他的双手,&ldo;筑防!没死的都起来筑防!&rdo;
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躺倒了,呵呵地乐。
康丫对我说:&ldo;想逃工啊?又偷懒?&rdo;
我有点儿歇斯底里地轻笑,并擞着他发出他不明其意的吠声,&ldo;汪汪。&rdo;
&ldo;别碰我的伤啊。&rdo;康丫说。
我拨拉开康丫那条炫耀般横在我旁边的腿,它中了跳弹,&ldo;贱人贱命,一个找死货打这种仗才被啃到一口。你爹妈还真给你改了个好名。&rdo;
康丫居然笑得颇有豪气,一边带着咳嗽,&ldo;贱?老子有汽车开那会,油门一响黄金万两,你们这帮路边蹭的才贱过灰老鼠。&rdo;
我忽然愣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瞪着康丫,康丫轻轻地压抑着他的咳嗽。
我沉默着在他身上寻找,我找到了,日军的第一枪就击中了他的肺部,伤口冒着血泡,而我一直以为他仅仅被跳弹啃掉了腿上的皮肉。
康丫咳着,给我一个苍白而无奈的表情,&ldo;有绷带的没?&rdo;
&ldo;……兽医!!&rdo;我大叫。
我从望远镜里看着。死啦死啦在一个遥远之极的距离喝叱着‐‐阿译带着帮身上没有硝烟痕迹的人在挖散兵坑,用少得可怜的一点儿工兵工具,他们连刺刀和饭盆都用上了‐‐距离很远,叱声却就在耳边,&ldo;林营座,这是你们为弟兄们挖的坑,你自己蹲下试试。&rdo;
阿译只好蹲了,那坑又窄又浅,阿译只好抱了膝,像极了拉屎,而且整个脑袋很无辜地露在外边。
死啦死啦责问他:&ldo;要擦屁股纸吗?这是屎坑还是散兵坑?弟兄们把命交给你们,你们只负责屁股?&rdo;
阿译只好苦着脸,&ldo;工具太少了。这土又硬,硬胶土。&rdo;
&ldo;列位在受罚,山顶开打,你们还爬在半山腰,让你们的袍泽兄弟以寡击众,如果他们也像你们一样差劲,我们已经被日军分几口吃掉了‐‐看得出你们很抱歉,能不能让你们的歉意变成够深的散兵坑呢?&rdo;
&ldo;能……可我不是怯仗。&rdo;阿译说。
死啦死啦说:&ldo;真好,我知道你们是体质嬴弱,营养不良,可还有一个体质羸弱营养不良的死瘸子居然一直跑在我的身边……&rdo;现在他看见我了,便遥远地指着我叫嚣,&ldo;孟烦了,我不是在夸你!你那样反拿了望远镜,是觉得离我远一点儿比较安全?&rdo;
我悻悻地放下望远镜,让一切回到一个正常的距离。
&ldo;去检查阵地!我会来找你麻烦的!&rdo;死啦死啦看了眼仍死心眼儿在坑底使劲儿的阿译,&ldo;挖不下去你也垒不上来吗?从这往上垒呀!我的营座爷爷!&rdo;
我连忙在他还没工夫来找我麻烦前走开。
我用望远镜看山腰的林子,日军不见踪影,树枝刚动了一下一发子弹就飞了过去‐‐我用望远镜看脚下的蛇屁股,让他更加丑怪,刚才是他开的枪。
蛇屁股在望远镜里冲我咧开一个海阔天空到铺天盖地的笑容,&ldo;小鬼子改娘娘腔了,光挨打不还手。&rdo;
我嘱咐他:&ldo;节省子弹。&rdo;
我走开,走向山的另一侧。我所过的地方迷龙正拿着他的机枪在发愁,这家伙总拿机枪当开山大斧使现在可招了报应,俩脚架砸成了一脚架,显然他是再无法固定射击了。
&ldo;咋整?&rdo;
&ldo;找日本天皇赔。&rdo;我说。
迷龙呸了我一口,而豆饼怯怯地把几个备用弹匣给他。
迷龙立刻开始发威,&ldo;老子冲锋陷阵的时候你跑哪里去了?&rdo;
豆饼如临大祸,&ldo;爬爬爬爬……。&rdo;
我趁早走开了,但身后殴打声和呼痛声仍不绝于耳。我扫视我们这个阵地,说真的,对攻击意志旺盛的日军它是居高临下的宝地,对只有防御能力的我们它可真不咋的,不仅因为阿译们的散兵坑始终深入不下去,更因为它在一个很容易被炮兵收拾到的山顶,光秃秃的一览无余‐‐我甚至觉得它还不如山腰上日军退进去的林子。一些石头大概是仅有的天然掩体,里放下一些伤员后就基本没什么站脚的地方了,那里现在被郝兽医占据着,不辣坐在康丫旁边看热闹,而郝兽医在擦汗,我过去看康丫,他恹恹地瞧着郝兽医捣咕他的伤口,一脸的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