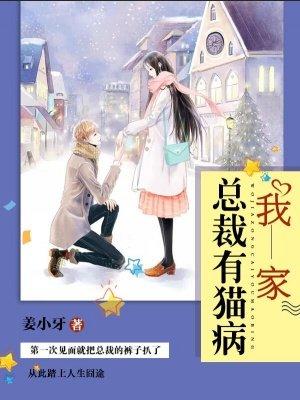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走火枪电影 > 第298页(第1页)
第298页(第1页)
贺家在国内呼风唤雨几十年,还在两国边境靠近塔邦这一边开辟了近千亩罂粟园,经营着配套的制毒售毒产业链。全村男女老少从事这项事业,仰仗贺家的庇护,一直经营得很顺当,这座贫困的村落家家户户都衣食无忧,甚至不少人一夜暴富。提前打过招呼,村头蹲着一个塔邦当地的男孩子,细瘦黝黑的胳膊腿儿,眼睛很大,亮晶晶的,望见贺罹一行人行色匆匆地徒步靠近,兴奋地跑上去迎接。阿琴认识他,用当地语言与他交流。那男孩用塔邦语对阿琴说了很多,阿琴听后,愤怒得摔下包裹,转回来对贺罹说:“丁哥他们都撤了,接应我们进城的人不见了。他们听到西南地区的警力调动的风声,还说动了塔邦的警察参与配合,现在谁也不敢来。”男人脸色沉郁,然后看向他手下背上的oga,宋知习沉睡着,眼皮微微合上,面色苍白几乎透明,表情是不设防的松弛,对外界的一切都毫无感知。这伙人的齐刷刷开始暴躁,原本到达目的地之后的喜悦和希望全被这个消息打垮了。“如果早一个星期到,就还有机会。”阿琴狠狠咬着牙道,“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去找这个姓程的。”蒜头死死瞪了落在后面的程廿一眼,骂道:“妈的,害人精,老子一枪送他归西。”“住手!”贺罹道。下属质疑去寻找程廿的做法就是在质疑男人的决定,绑架程廿是为了寻找宋知习,他的确达到了目的,找到了人,代价却是断送了逃命的时机,下属们难免有所怨言,却只能对程廿发泄愤怒。贺罹当然不在乎人质的死活,但是现在还不能让他死,他不想等宋知习清醒过来后质问自己为什么杀害他的老师。此外,不知道为什么,赵家貌似很看重程廿,留着他也许还有用。“进村,先修整半天再说。”贺罹下了命令。这伙人进入了那个叫米登的男孩家里,受到了款待。男孩的父亲和叔叔掌握了整个村子的毒品销售业务,靠着贩毒生意致富,十分感激贺家。贺家早已大厦倾覆,他们还倾力帮助贺家人,不知是真的心怀感恩,还是愚蠢到相信贺家还能东山再起。程廿被关在一间卧室里,贺罹一行将近十人,在隔壁房与米登的父亲开始商量接下来的去向,大部分人语言不通,由阿琴作翻译。还没商量出个结果,米登突然风风火火冲进来,打断大人们凝重的谈话,用当地语言喊道:“警察来了。”听到消息,这伙恶贯满盈的匪徒大惊失色:“混蛋,怎么来得这么快?”阿琴脸色惨白看向男人:“我们快撤吧!”蒜头低嘲道:“没了引路人,还能撤去哪?猫进山里躲一辈子吗?”“来不及了,老子跟他们拼了。”外国面孔的壮汉扛起枪往外冲。阿琴:“别冲动!”“娘的,那让我先宰了那两个娘儿们!”阿琴死死压住门,才让他冷静了些。贺罹盯着桌上古旧残破的地图,一言不发。砍哥看向贺罹,他是这伙人里年纪最大,资历最丰富的顶级雇佣兵,但他也一样受雇于贺家,听命于贺罹。他低着头,冷静道:“两个选择,第一,进山,赌一把运气走出林子,但是不能带着那几个累赘,第二,”他用手点了下地图上水库附近的某个点,“没人带路,我们自己进去。”一圈人都在注视着男人,而男人盯着地图上那个红点,半晌沉默。进了那片原始森林,没有五至七天是走不出去的,食物水源无法保证,光蚊虫就能要了人的命,宋知习撑不过去。如果选择这条路,他只能放弃好不容易找回的oga,将他留在这里,连同他肚子里的孩子,他的亲身骨血。如果是第二条路,未知性太高,搞不好所有人都交代在这儿,他不能用手下的性命来冒险。所以,男人的最终决定,所有人自行选择哪一条路。一时没人说话,他们都是刀光剑影里出来的狂徒,然而却被逼得没有了活路,面对生死关头,没人会轻松地抉择。砍哥道:“头儿,你拿个主意。我跟着你。”“我也是。”阿琴道。阿琴都这么说,蒜头只能做出一样的选择。到最后,大部分人容易跟他赶去地图上的位置,只有两个人选择扛着枪支和物资跨越密林深山。程廿刚眯了会儿,就被人粗暴地摇醒,坐上当地居民采摘罂粟果实的简陋的三轮车,摇摇晃晃驶向深山。来到一个砌着褪色红砖的山洞前。男孩米登把他们领到此地,又对他们说了很多,似乎在警告着什么。但是除了进去找条生路,他们已经没有选择,米登最后还是离开了,坐在三轮车后背上,用忧心忡忡的眼神对他们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