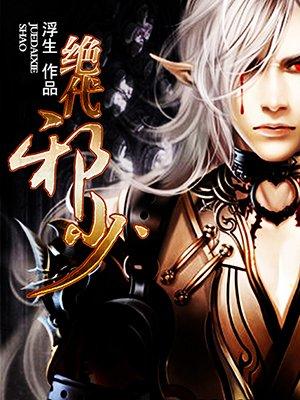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 第189章(第1页)
第189章(第1页)
他盼她懂他的心,未料当夜惹来了勃然大怒的亲王,称沈家欺人太甚,必揭发沈家勾结同盟会之举。
是夜,他颓然趴在祠堂的板凳上,浑身鞭痕交错,沈邦将信纸摔到了他脸上,怒斥自己的儿子幼稚可笑,以为区区几行字就能打动格格,格格丝毫不为所动坚持退婚。
沈邦走后,他从凳上翻身而下,爬行数步,才勉力够着了那张皱巴巴的纸——早已面目全非,如同他背上绽溃的肉。
继而,是没日没夜的高烧与昏“迷”,不知过去多久,醒转时整个沈府红光映辉,他看到了大红门上粘金沥粉的红双喜,府中唯一的亲信告诉他朱佑宁被捕,死在了狱中。
满目鲜红成了满目殷红,亲眷们前来同他说“恭喜”,他茫茫然,不知喜从何来。
伤口并未愈合,所幸新婚吉服亦是红“色”,拜堂时也没有人发现端倪。
那个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子,终成了他的新娘子,他在推开新房大门时,心里却生了恨。
恨她糟践自己的心意,恨自己错付于她,恨友人错付的自己。
可掀开她的红盖头,看她的珠钗被他打“乱”,竟还想着为她戴好?
他恨自己无用。
在听她说出那句“非我心仪者”时,世界坍塌,他对她说出了这一生最狠厉的话。
当机立断,何以未断?
每一字,每一句,既是戳她的心,也是剜自己的骨。
珠钗刺破了掌心,他“逼”自己做出决断。
逃婚,是为了离京救人,不告而别,是少年对少女的割舍。
成功救出革命党人是不幸中的万幸,踏上邮轮前,沈琇写下了两封家书。
一封是为了“迷”“惑”父亲,误导他自己要去美利坚,另一封……是给她的。
其实离京后,他曾自问,既奔往血路,何以要强求她的支持,祈盼她等他呢?
想要退婚……是她的权利,她的选择,被迫嫁给不愿嫁的……他,她亦是受害者。
沈琇一遍遍说服自己,看似通情达理,却不敢承认,这是为管不住心的自己找的借口。
饶是写废了几张信纸,有决绝的告别,有假作放下劝她离开沈家的淡然,但无法寄出。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为何会在一封诀别书里,写上“如愿等我,我必归来”这样的话。
而后,抵达香港时的浑沌,收到电报得知她未离开沈府的不可置信,再度北归时的忐忑与憧憬,一切一切,历历在目。
直到回到家,回到东院。犹记去时霜叶红,归来天地缟素白。
白“色”的雪,红“色”的天,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人生底“色”,也是……唯一的“色”彩。
“沈琇?沈琇……”沉溺于红与白的天地,听到有人在遥遥唤他,“沈一拂!”
云知的手胡“乱”的往前探,始终听不到回应,急得爬起床叫来福瑞,福瑞听到动静冲进来,“二少爷是不是又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