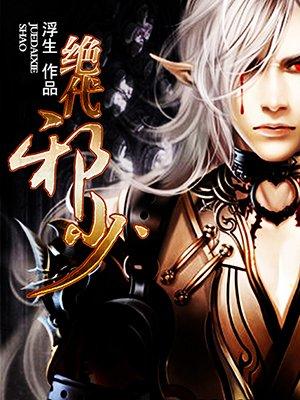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 第149章(第1页)
第149章(第1页)
他寻的专注,没察觉云知满面的难以置信。
沈一拂加入过同盟会?这……这怎么可能呢?
“找到了,在这里。”马老从柜子上取下了一个相框,放到书桌上,“瞧瞧,认不认得出哪个是你父亲?”
林赋约的相貌很好认。
最左边那个身着黑色褂衫的就是。比祖父书房里那张大合照更成熟稳重些,而站在最右的沈一拂——身量高颀,眉目澄澈,梳着那时最兴的背头短发,正是琉璃亭那次他的模样。
照片陈旧,依旧能看得出四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眉目带笑,眼里仿佛都透着无限的希望,哪怕时隔多年,只需看一眼,也知他们相交甚笃,志同道合。
马老看她看得出神,坐回椅背上,道:“你翻翻看照片背后。”
她拆下相框,但看背面的钢笔苍劲有力写着一行字:革命流血,自吾辈始,前仆后继,信仰永续。
云知心念巨震。
“本来我不赞成你爸爸冲在前沿,嘱托他保重己身,方能将所学的知识蔚为国用,时值湖北各革命组织欲要起事,他在文学社和共进会中都有同窗,就义不容辞留下调停,之后就寄了一封信加上这张照片给我。”马老摇头失笑:“我啊,当时人在外地,急的团团转,也真是奈何不了他。”
她迫不及待地问:“之后呢?”
马老本只是追忆,看她神色不觉一愣,“你父母没同你说过?”
她捺低了声音,“我小时候在苏州老家那边,这些……我爸妈很少和我提。”
马老“嗯”了一声,道:“为人父母,自不愿之女走上同一条路。同盟会分散后,我与你父亲就失去了联络,见到了你,想起第一次见你父亲,他也就这般大……”
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故人已故。
“人老了,越早的事记得越清……”马老叹了一声,“我听说你父母是前阵子在一个小村庄里亡故的……”
“是意外,旱了一个多月,走水了,我从家里的水管里爬出来的。”祖父嘱托过多次,不论在什么人面前,都要一口咬定火灾只是意外。
马老活到这把岁数,小丫头脸上一点异色不是没看在眼里。他终究没有深究,只道:“好在你平安,你父亲也不算后继无人。”
云知将照片放回相框,起身朝马老恭恭敬敬鞠了一躬,“我会努力向学,带着我父亲的那份,不会令您失望的。”
她心底仍有许多谜团,但看马老眼眶微润,不敢再询。
直待跨出办公室,耳畔还有些“嗡嗡”的声响,分不清是耳鸣还是心颤。
马咏老教授一席话令她的心房几处空几处堵,一时不知从哪填从哪疏。
近日心中念念的前尘的因,竟以这样的方式得知了些许果。
云知转向身后红砖砌筑的红楼,周围的景致恍恍惚惚的晃过去,思绪逐渐变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