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页小说站>共济失调走路不稳吃什么药 > 第28章(第2页)
第28章(第2页)
杨河的电话先是说了一切都好,专家住宿和明天课程都没有问题,然后问他身体的情况。
“死不了,”容闻良闷着声音,如同骤雨过后一样潮湿、绵软,“明天早上你也给我好好看着,说不定去不了。”
他压着嗓子咳了两声,却不知这场雨下在了电话那头的宋辞心里。
挂了电话杨河的肥脸都皱在了一起,“老容一个人在家,我晚上得陪专家走不开……”
“我去看看吧,”宋辞轻声说,“正好我身上没有安排事情。”
·
按照杨河提供的地点宋辞开车到了容闻良家门口,备忘录里记着一小串数字,明明能倒背如流,他还是照着手机一个一个输入密码。
杨河给容闻良打了招呼,说叫个人过去,没有说是宋辞。
其实研二上半学期他来过这里,那时候容闻良搬新家,因为年末货拉拉没有上门服务,他们几个人搬了一整天才结束,最后在主任家里喝酒吃烧烤,他第一次醉得记不清自己到底怎么回去的。
进门后他摸黑开了灯,容闻良的卧室在二楼,他脱了鞋光着脚,带着酒精和棉球上了楼。
主卧很大,除了衣柜和电视就是床,容闻良闭着眼睛陷在柔软的床上,宋辞轻轻喊了一声,没有人回应。
床边放着一杯热水和退烧药,他想容闻良应该吃过药,用手背探额头的温度却依旧有些灼热。
他用酒精仔细擦拭容闻良露在空气里的皮肤,四十多岁的男人睡得不太安稳,他的动作很轻也很温柔,生怕把人惊醒。
重复擦拭了三遍以后,容闻良的体温好歹降了下来,宋辞用棉签蘸水涂男人干裂起皮的嘴唇,见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握住容闻良的手,轻轻用脸贴了贴,跪坐在床边看着近在咫尺的心上人,忽然想亲一亲他。
他好像糊里糊涂地爱了他三年,除了对方的“特殊照顾”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他决定偷一个吻满足心底的不甘与不平,然后再也不要被杨河一句明知是诓骗的“老师想见你”轻易钓回来。
夜里空调的温度吹得宋辞手脚冰凉,但很快又冒出一层薄汗,他谨慎小心地趴在枕边,低头去够那个微热的吻。吻还带着棉签沾上的水,两片唇含糊地碰了一下很快就该分开,可一向幸运的宋辞遇上了平生最倒霉的时候——容闻良可能要醒了。
他被捉住了手臂,对方似乎不满足于点水啄吻,轻轻试探过后,竟然用力封住他的唇,用舌头卷尽他口中的津液。
宋辞害怕了,挣扎和呜咽打断了容闻良,手里的滑腻肌肤和迎面落下的温热呼吸让男人清醒不少,他哑着声音说:“……是宋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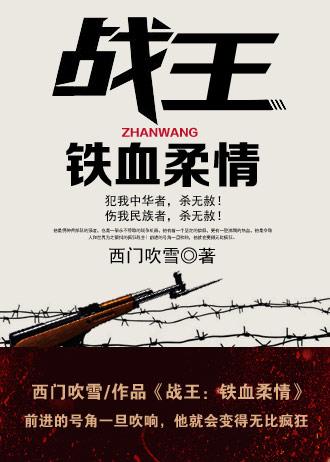
![真男人不搞假gay[星际]](/img/13693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