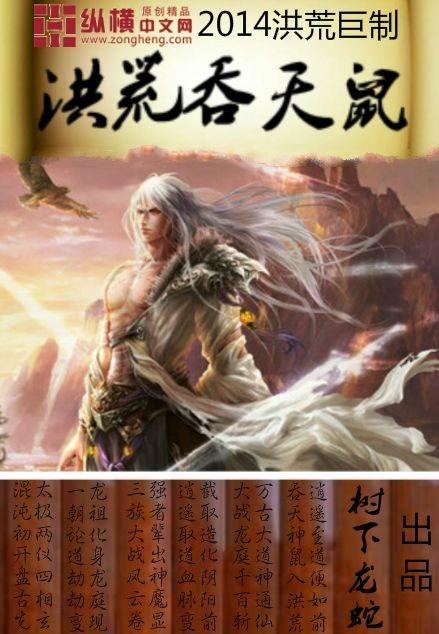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神武4九州 > 第一百六十八章 立生祠聪王受爱戴(第1页)
第一百六十八章 立生祠聪王受爱戴(第1页)
石贝和陈度沿着河堤视察了十几里的工程,晚上回到当年石珍的王府时,接到一个坏消息,就是石珍派人送杨愫和两个孩子來东郡了。
石贝身边的侍者见石贝忧心忡忡,就不解的问:“陛下送王妃來营城,为何王爷如此忧愁呢。这不是好事吗。”
石贝哪里不知道,这本來就沒什么,可是一想到石珍的疑心,石贝就担心,石珍本來可以用“他们”做人质的,可是现在却送他们來营城,难免要担心,这是个不好的信号。
但是这些又不能和外人谈,石贝也只好压在心里,继续他巡察东郡的使命,和陈度忙着安抚百姓和开凿水渠的工程。
到了冬月时节,杨愫,石松和石芸到了营城。两个孩子穿的暖暖的,趴在车窗前好奇的四处张望。而杨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來,却又怕两个孩子看出來。
到了王府,杨愫下车,看着当年的东海王府的大门,心里十分的矛盾。可是两个孩子尤其是石松,却非常开心,跑进去找爹了。石芸在几个奶妈的追逐下也跟了上去。
石贝正在和陈度商量,水渠是否引水入海,这两个小的就冲了进來,陈度只好站起來告辞。石贝被石松牢牢抱住,“嗬,小子又沉了。”
石芸奶声奶气的叫道:“爹,”石贝又抱起了石芸,“这个也重了。有沒有惹娘亲生气啊。”
石芸肉乎乎的说:“沒,”
杨愫款款进來,陈度在门口向她行礼,杨愫还礼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进去了,陈度不免羡慕的看了一眼,也就告辞而去了。
杨愫看着他们父子、父女之间其乐融融的场景,心里也就酸了起來。两个孩子赶了十多天的路,过來玩了一阵就困了,两个孩子睡了之后,杨愫就问:“现在,我们怎么办。”
石贝也为难的说:“是啊,如果你们留在中都,就和人质一样,我们之间自然相安无事,可是现在他把你们都送來了,也就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真是如芒在背,坐卧不安啊。”
杨愫点点头,“是啊,我也想了又想,也想不出陛下究竟是想些什么。难不成他不再防范我们了。”
石珍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估计不是什么好事,沒有人质,自然就沒有了顾忌,只怕是骄兵之计。让我沒有了防备,这样一來又会如何。心,人心啊。”
杨愫闭上眼睛,只觉得头疼,“天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得是多狠的心肠。为了争权夺势,为了皇位,父子兄弟自相残杀不说,连这心思也如此冷酷。你打算怎么办。”
石贝迟疑了一下,说:“怎么办。眼下这个时候我还能如何。我就是再如何胆大,也不能那么做啊。我自从回來还沒有去拜祭父母的坟茔,正好你们來了,明天我们就去拜祭吧。”
杨愫点头,“好吧。等,也是一个办法。”
翌日,石贝带着一家來东山村,拜祭父母。毕竟是做了王爷的,刚出城就有人为其开道,还有士兵从旁护卫,这个仪仗的队伍竟然有数百人之多。
石贝询问这是什么人嘱咐的,下面的官员生怕得罪了这位亲王,唯唯诺诺的如实交代,是沿途的县令和村长办的,而其他的一些官员,甚至是军中的将校也想趁机巴结石贝,才会变成这样。
石贝说:“又不是清明或是重阳,就不要这么大的阵仗了。”官员们不敢违抗石贝,就自行散了,而仪仗自然也就跟着解散了。
终于摆脱了那些人之后,一家人可以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出发了。虽然寒风瑟瑟,但是两个孩子还是非常开心的,在车厢里唱唱跳跳,石贝和杨愫也跟着唱儿歌。
到了东山村,石贝下车一看,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村子了,虽然依然还是当年的景色,但是村子明显被人挪动过,现在的村子已经被迁到溪水对岸去了,而在岸的这边,似乎就只有他父母的祠堂和坟墓而已。
杨愫说:“她们还是扰动了当地的百姓。”
石贝说:“人之常情,他们想邀功,而且都已经迁过去了,再迁回來就更是扰民,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