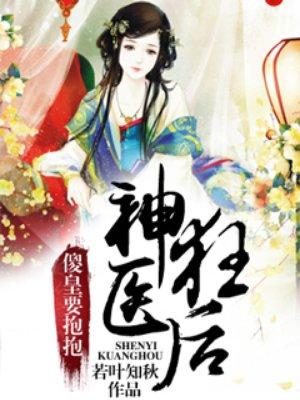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嚣张最新章节免费阅读 > 第五十五章四个字两个人No 298No 303(第2页)
第五十五章四个字两个人No 298No 303(第2页)
“没什么,”余淮看向窗外,若有所思,“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他都能说放就放,我还纠结个屁啊,我比他差在哪儿啊,对不对?”
我眨眨眼,慢慢明白过来。
余淮的这道坎儿,终于算是过去了吗?
我笑:“得了吧,你就是看他也没法儿保送了,心里特爽吧?”
“滚,”他被我气笑了,“好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我们在校门口准备道别。才五点钟,天已经黑下来了。他在路灯下朝我笑着摆摆手,转身就要走。
“欸,余淮!”我喊他。
他转过头,不解地看着我。
“对不起。”我说。
余淮的脸抽了抽。
“你听我说,其实之前,我看得出你很努力地在调整自己了,可我还在旁边每天哭丧个脸,希望你能过来找我倾诉……我觉得自己挺没劲儿的,你吼我的那句话是对的。我也想说声‘对不起’。”
他笑了,一脸不在意。
“得了吧你,这只能说明两件事,第一,我演技差;第二,一个大老爷们儿为这点儿破事儿缓不过来,真够丢人的,还迁怒于你,更丢人。行了别提了,赶紧回家吧。”
我认识的余淮正式回归,依旧是当初那个少年。
“你才多大啊,就说自己是大老爷们儿。”我笑。
“哦,”余淮一拍脑门儿,“忘了你属虎,你才是前辈啊,我是大老爷们儿,你就是大老娘们儿。”
“你才是大老娘们儿!”我把手中的空咖啡罐朝着他的脑门儿扔过去,被他哈哈哈笑着接住了。
No。300
四月的时候,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
即使对四季更迭早就习以为常,春分谷雨,万物自有定时,又不是第一次见了,然而每一年、每一个季节,照样可以有某一个瞬间惊艳到我。
比如一夜温润的雨下过之后,早上我无知无觉地走出门,风好像格外柔和,我置之不理;它再接再厉,我麻木不仁;终于它将路边垂柳的枝条送到我面前,一抹刚抽芽的、令人心醉的绿,懵懵懂懂地闯入我的视野,轻轻拂过我的脸颊。
我的目光追随着它的离去,然后就看到大片大片的新绿,沿着这条街的方向,招呼着,摇曳着。
世界忽然就变成了彩色。
那些兵荒马乱也随着冬天轰隆隆地远去。
保送生和自主招生的笔试过后,各大高校的二轮面试也在春节前纷纷告一段落。
我的北京之行变成了一趟废物之旅。可能我本身就没有学艺术的潜质,跟电视和电影都注定无缘吧,每所学校的排名都很靠后,基本没戏。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爸妈,虽然他们还是说意料之中,说没有关系,我却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
有时候在课堂上睡着了,爬起来的时候眼睛会有点儿迷糊。那几秒钟的恍惚里,我会突然想起程巧珍,想起那间四处漏风的砖房,这让我能在暖洋洋的教室里面忽然头脑一片清明,像是那天的风从北京一路吹过来,吹散了眼前的迷雾。
成绩在磕磕绊绊中上升。每天晚自习过后,余淮都会和我一起悄悄地溜到行政区顶楼,因为那里方便说话,不会吵到其他上自习的同学。我每天都会整理当天算错的题目,余淮一道一道地耐心给我讲。在我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开始背诵文言文课文和古诗词了,也许是不再有竞赛保送护体,他也学会了收敛。
当我煎熬在黑色的冬天时,日子总是过得很慢,可一旦努力起来,有了起色,时间却走得飞快,像是生怕再给我多一点儿时间,我就会变得太过出色,一不小心吓到老天爷似的。
然而奇怪的是,后来每每回想到那段岁月,总会觉得,时间慢得好温柔。
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个晚上他讲了哪些题,骂了我哪些话,我又考了他哪句古诗,他又背成了什么德行。
如果非要说我硬着头皮学理是在余淮身上浪费了两年时间,那他又何尝不是把自己很多宝贵的复习时间都浪费在了我身上。
我们都从没因此而向对方索取什么。
No。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