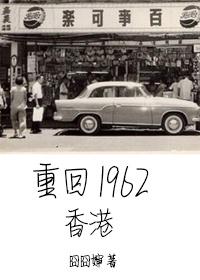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18号酒馆 > 第6页(第1页)
第6页(第1页)
“这个条件你们觉得如何?”我一言不发打开电脑做了一张模拟图,一千万美金凑一块那是多大一块绿砖啊,换算成越南盾什么的呢?就算泡nasa妞实力不够,长两条腿的应该都可以试试看了吧。但约伯没有露出和我一样的星星眼。他沉默地想了半天,看样子是在天人交战,所以一时怒目圆睁,一时如丧考妣,最后他对我断然一点头,“不行。”“昨晚那把刀可是差点砍中了我的脖子!”他夸张地比画了一下,“大动脉!”约伯站起来点点头,“你太太摆明了是要斩草除根的,买通了全世界最恐怖的专业杀手,你藏得了时藏不了一世,她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我本来以为这一单只是单纯救人一命,换点现金.现在好像要变成救人一命搭进去老子全家的样子。”“这种生意太亏,我不做。他拍拍我,“建酒馆的钱我找高利贷凑一凑我们把他扔出去吧。”我和大卫都吓了一跳,“扔出去他就死了喔?”约伯表示他不关心大卫的死活,而且如果我不支持他的决定,他很快也会不关心我的死活老实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完全跟看死人一样,半点主客之间的感情都没有。他说完这句话,头也没回就走了,就算我在后面代替大卫喊出“最多一人一千万”,他也去如流星,竟然没有诈和的意思。我和大卫迪,面面相觑,他风度不失,只是微微一笑,说:“人各有志。”问我:“你一个人行不行?”这纯然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啊。我摇摇头不答话,心中痛惜与那千万美金的有缘无分,我治病可以,惹杀手就不够料,所谓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古人绝对不会欺骗我。给他换了药回到书房,正要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再想想明白,忽然秘密神医咪咪兄在skype上叫我。“怎么,帮我查到j是谁了吗?”“还在查,我找你说另外一件事。”“收钱。”“操。”“你会有什么事来问我啊,号码百事咪先生。”“昨天晚上出了一个多人遇袭事件,受害人一共十一个,全部是被重物撞击后脑打成植物人,现在有法医私下联系我要会诊,你对植物人有研究,我说转给你赚个外快算了。“全部植物人?凶手喜欢码清一色是吧,哪儿的事?”“你们那儿。”这四个字一出来,我心里就一紧。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浮上心头,刹那间我声音都变了,“昨晚?什么,什么时候?”“我看看,嗯,十二点半到夜里两点之间,时间段很密集。”我把耳机往桌上一摔.旋风一般冲了出去,在门口摸出电话来刚要打给约伯,他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出大事了。”我马上知道自己的预感被应验了。【6】我上街买了今天的全部本地报纸每盖,每一份的社会新闻版都登了这件事,受害人在不同的街区遇袭,出身背景性别经历都无近似之处,不但自己有口难言,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警方初步调查得到的就是一头雾水。但我和约伯当然能一眼看出,这些都是十号酒馆的熟客。就是天天都见到,但从来不跟彼此打招呼的那些人。大个子的胖二哥开出租车,他每天来酒馆坐着,不喝酒,而是等着把那些喝得差不多的单身客人拉回家去,他不爱拉陌生人,有陌生人来找他做生意,他能跟人家打起来,然后再没奈何地拉人家去医院。帅哥小保爱喝波本,喝得差不多就会到酒吧中心的小乐池唱歌,嗓子烂得不行,不管唱什么都是一个调调,还以为自己是绝世名伶,这个习惯让他没法在其他地方生存,只有十号酒馆的人抱着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坚韧态度任他胡闹下去。花爷是最穷的酒客、年纪大了,干些力气活,要一打啤酒能喝一个多月,常常要求存半瓶酒,约伯给他存了,第二天就换瓶整的给他。他爱喝酒,更爱攒钱,攒到一个整数就买成吃的穿的拿去东城孤儿院派,他以后要是死了,肯定一大群孝子贤孙披麻戴孝,虽然没半个是他亲生的。有钱的是乔乔,特腼腆个孩子,刚会喝酒就扎到了十号酒馆,从没挪过窝,他老帮人买单,还买得很羞涩,生怕人家不好意思,买完就溜了,要坑他没别的办法,只要站在桌子上指着他逃跑的身影大喊“是乔乔给的钱啊十二号桌,记住了哈,”他就会恨你一辈子。十号酒馆烧了,我没觉得有多严重,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奇怪,一开始你觉得去的地方很重要,到最后才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和你一起去,待在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些人。一夜之间,都瘫在床上,眼睛闭上了,不能再喝酒了,不会再笑了,不会再来十号酒馆了。见不到他们了。如果我不是运气好,住得又近,我今天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约伯不是突然想去偷鸡摸狗,他已经葬身火海成了一块焦炭。我整个心,都掉到里去了。我在家门口等了十分钟,约伯回来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交换了个眼色就并肩往烟墩路十号走,灾后的废墟还是那副懒懒散散没救的样子,约伯难得地拿出一根烟点燃,抽了没两口,说:“那么,这事儿变了。“我点点头。突然之间这不再是大卫的事了。这变成了私人思怨。我们的私人恩怨,十号酒馆的私人恩怨。那么就要用十号酒馆的解决办法。他继续抽烟,慢悠悠地说,“你,护照还有用吗?”我继续点头——总有一本有用嘛。他表示赞许,“那么,给我,三天内我搞定去纽约的签证和机票,你,在那边找个地方我们能住一段时间。”这意思是?“烧了我们房子打了我们的人就想这么算了?门都没有,我们去抄他们老底。”我热血沸腾。“我同意!!”不过,就凭咱俩?没一个能打的喔。他很鄙视地说:“这是智能时代好吧,你以为还在混斯巴达三百勇士?”约伯,指了指他的脑子,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深邃的神情,半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不用打,就靠这儿,我非玩死那个蛇蝎女人!!”我简直想啪啪鼓掌,太帅了啊约伯,没见过你这样啊,你天天蹲吧台后面擦杯子擦得那么不敬业就是因为你其实在想这种拉风的台词吧。他承认,“想了不少,没啥场合用。”约伯猛拍我肩头,“三天后出发,你把那个啥大卫安顿安顿,第一给点药吃吃稳住别死,第二得关起来,不能叫他坏了我们的事。”分手之前,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管硕大的喷漆,在十号酒馆仅存的一块白色外墙上画了一个苹果,手法很抽象,苹果中心写了一行潦草的字:reven。我在一边说意思是,iphone用户对此事件负责吗?”纽约。纽约。天气开始变冷,每天都出太阳,但那太阳像假的.金黄,灿烂,唯独照在身上毫无暖意。我和约伯坐在第八十七街街口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里,他慢慢吃一个辣卷饼,而我定神看着玻璃窗外的路。我们在等人。等一个叫玛利亚的女人。一个半月前我们到达肯尼迪机场,我带着约伯直接杀到咪咪兄住的公寓,令他心灵受到极大惊吓,那栋楼门禁森严,看门人目光锐利如隼,对外人态度凶残,但约伯跟他只聊了大概一分钟,对方就死心塌地认为他是那个搬过来才一个多礼拜的住客,还殷勤地过去帮我们按了电梯。我对约伯这一手司空见惯,有时候他卖给我们水,大家还是在那儿很high地喝得大醉,这种催眠一般的人格魅力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