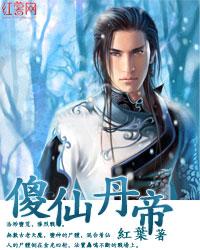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津女记者案件 > 第196章 踟蹰不定(第1页)
第196章 踟蹰不定(第1页)
“我是这么想的,官员贪墨与特务在津门制造假民意不能以同一办法来解决。日本企图染指中国内政,而两国关系毫无疑问是会影响国际秩序的,香江又是连通国际社会的一个窗口。因此我想,那位记者选择在香江出刊,是出于争取国际上正义力量的考量。可回到你所提的问题上来,贪墨固然可耻可恨,其本质却是中国内部社会的问题。自己的事该自己办,无需外人插手。你想,既然两件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就没道理依样画葫芦地向外求援呀。”这时,厉凤竹说完了话,又开始止不住地点头,仿佛是在赞许自己艰难而成功地渡过了一个难关。
坂本闻言,不由苦笑:“你质疑我不该不动脑筋地如法炮制,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试图发动过多少内部力量。有能力的不愿出头,愿出头的不在其位。津门有如此多的寓公,你恐怕也是知道的,许多能人贤士之所以郁郁不得志,完全是为着党同伐异……南京的高官,还有谁记得当初北伐时所说的誓言?从南至北,那样劳民伤财一通折腾,如果只是为了换一批人吸百姓的血,那还不如一切照旧呢!都说北洋旧人贪婪无能,可我看如今的境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写的长信没有数百封,那也又几十封了。有回信的都是些北洋旧臣,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正是这寥寥的几位,向我建议先去发动报界的能力,等到民间有了热议,他们再以个人名声帮助我推动此事的调查。”
厉凤竹见自己无论抬什么样的理由出来,坂本都要回敬一长篇的大道理,觉得他的恒心是难以撼动的。长久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只好改了个主意,实行缓兵之计:“容我考虑几日……”
这几个字虽以万般无奈而艰难的语气缓慢吐出,可听在坂本耳中,已是天大的喜讯,忙拱起手来,道:“哎呀,这可真是……”
可厉凤竹也是同时地抬手一挡:“不忙谢,我有个额外的条件。”
坂本咽了咽满腔满腹的感激之词,表示出最大程度的顺从:“你尽管开口,我都答应就是了。”
厉凤竹颔首,先端起杯子来,接连呷了两口咖啡,方才接着向下说:“我们报馆近况不佳,这也是我改换风格的一大原因。而你所托之事,既不是一天两天内就能争出结果来的,同时也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要你答应我,考虑的时限由我来定,不许你催促干涉。”
理由并非不充足,只是这时限是不定准,一两个礼拜是等,一两年也是等,可坂本只是来此度假,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他其实等不及。然则才刚掷地有声地满口说着大话,立时就要收回承诺,实在也是张不开口。因之,坂本非但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了,嘴上还得表示着感谢。然而心里有一阵挫败和失望,兀自盘算着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可以寻,这就不愿在此地久坐,匆忙告辞离开。
至于厉凤竹,她认为坂本的正义和能说会道极容易动摇人的心智,故而心内紧绷着一根弦,眼神也跟了情绪飘忽起来,总不能安定地落在哪一处。因此,她只管站起身客套地握握手,别的一概不曾留意。当她目送了坂本离开,终于松了一口气往回坐时,却见坂本把账册给遗落了。待伸手举起,刚要张口叫人,却发现咖啡厅的大门只是晃动而不见人影了。
这也只能代他暂为保管,找机会再交还了。厉凤竹因想着,抬头环顾了一周,见是店内主顾并不多,倒落个轻松自在,坦然地翻开账册从头一页起慢慢地翻看。既看了,就阻止不了一名记者的本能,集中注意力来记忆着要紧的线索。只见她嘴巴一张一闭,手指虚虚悬在桌面上时不时空比划几下。这样静静地不过待了几分钟的工夫,她便警觉某个暗处射来一束目光正注意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因又想到,既然坂本会认为《真相》出自大公报社,难道别的日本特务就猜不到吗?会不会是有人正在暗中监视?
厉凤竹被自己的猜测吓得浑身直冒冷汗,蹭地一下弹起身子来,煞白的脸色把一双不停梭巡的眼睛映衬得格外乌亮。
只听角落里传出低低的一句:“您呀,坐了快三个钟点了,不续杯吗?”
扭头去看,心思稍稍放定,原来是这里的西崽在说话,倒没什么可疑的。不过,那人虽是来问续杯的,却没有拿着茶水单,两只手不断搓着表现出一种踌躇的样子来。
厉凤竹经他如此说,不免要低头看看手表,又瞧瞧那账册,早已看过了三分之二。不想在她未察觉的情况下,竟已混过去这么长的光阴了。脑子里依稀记得坂本抱憾告辞,走时十分匆忙,因就猜到了西崽在为难些什么。
“唔,不早了,还是会账吧。”
闻言,西崽脸上便堆了笑意出来。他早就有所察觉,这桌的一对人,聊并不投机,而那位早走的先生并没有什么绅士风度提出主动会账,只是很不悦地匆匆推门而去。至于留下的妇人,则像是钉在了椅子上,既不走也不点吃食茶饮,一动不动只管看书。先时还早,没什么客人倒也无所谓,可越近黄昏顾客就会越多的,有这么一个赖着位置不消费的主顾,很让生意人为难。因此,这里的老板就喊了西崽过去,看能不能把人请走。
###
当厉凤竹走出咖啡店时,差不多已是晚餐时候。想着这一阵子总是晚睡晚起,并不能与家人增进关系,便决定回家去坐坐。
饭桌上,厉老太太把一碟拌野菜端上桌,才坐下不到一分钟,抬眼瞧着女儿眼底坠着的眼袋,不由地减了胃口,咋舌叹道:“起先你对我说改了工作,不写从前那种要人命的文章了,我心里还欢喜呢,想着你不干那种苦差了,在家的时候就长了。”
厉凤竹正把碗筷分了三份,首先越过桌子送了一副在母亲跟前,对上她那充满忧虑的眼眸,苦笑着作答:“我只是改个岗位,却没有换职业呀。记者都是劳碌命,所谓的苦差和好差,不过是矮子堆里拔高个儿。别看我现在负责的是意在消闲的副刊,从字眼儿上解释,就是闲里找话。何为闲呢?无非吃喝玩乐,要在这几样事里找新闻,应酬自然就少不了。”说完话时,小如甫身前也就多了一副碗筷。
厉老太太则一边给外孙盛了齐平碗口的米粥,一边皱着眉说:“照你的话说还是份苦差呀,再改个活儿不行吗?我记得你安定下来的时候,不是一直干那种查错字的工作嘛。那种活儿既不危险,也不用出去喝酒跳舞,还有固定的收入。少虽少,还能凑付着每月的家用。说实在的,这会儿我是不用害怕你丢小命了,可我眼看着你时髦起来了,就要害怕你在钱的方面弄出毛病来。”
厉凤竹自是不回答,只是惊异地看着儿子那张比碗大不了多少的脸往下一低,呼噜呼噜两三口竟也把很稠的粥喝了大半碗下肚。
厉老太太见状很觉无趣,撇着嘴摇了两下头,自也闷头喝粥。
倒是小如甫抬了头,手背往嘴上一抹,问道:“妈,你过的是不是话匣子里说的‘纸醉金迷’的生活?”
厉凤竹听了,脸颊顿时憋得通红,赶紧把脸埋在粥碗里塞了一大口食物。如此一来,闭口不答也就顺理成章了。
小孩学大人说话总是这样,往外说的尽是些不合时宜的大实话,大人听一句难免要受半天的窘。
厉老太太向上一撩眼皮,先打量打量女儿,再盯了外孙那一双乌黑的眼,带叹带哼地低声抢着答道:“是吧……”
这一来,厉凤竹更是尴尬,倒学着孩子的模样把粥喝得呼呼作响,想把这话头避过去。
小如甫把干净见底的碗往前稍稍地一推,瘪了嘴角微露不快:“晨训的时候,校长说纸醉金迷是不好的风气。”
为他这一句雪上加霜的真话,厉凤竹心虚到直接把嘴里的粥呛在了桌上。
厉老太太觉得眼下的势头于己有利,自想着要尽一个长辈的义务,好好劝劝厉凤竹。谁料一抬头,见了桌上三个粥碗已然空了两个,倒是那盘野菜只挖走了一小半。厉老太太这就嗤地一笑,转了话头:“这倒省钱,三个人喝粥还吃不完一碟菜。可省这几个子儿,还不够晚上出去一趟的车钱嘞。”
无论这种对话是否成心,厉凤竹这时完全没有定力继续视若无睹了,赶紧地站起来在衣柜里挑挑拣拣,预备换了行头躲出门去。
却不料,喝完了粥一直不下桌的小如甫,又嘀咕上了:“姥姥,咱家里都好多天不吃肉了。”
那声音低虽低,又恰好地可以让厉凤竹听见。
看小说,630book。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