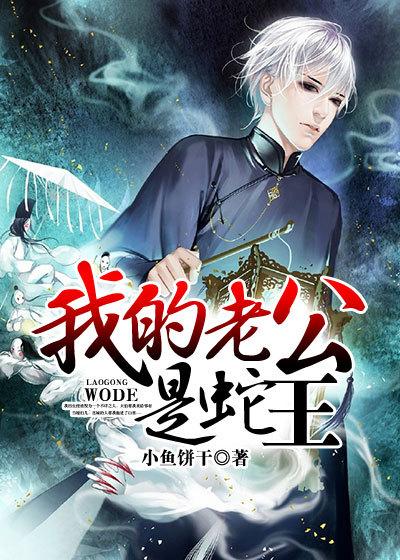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把陛下送进火葬场后格格党 > 第144章(第1页)
第144章(第1页)
“仙人说今日的药服完后,还要再服些滋补的药膳的,你可别忘了。”
她日日跟个管家婆似的在他耳边念叨,势必亲为,每每皆是把汤药捧到他跟前用她那双湿漉漉的眼睛迫他喝下那些奇奇怪怪的汤药,他又怎能忘。嬴昭把她冰凉的手卷进袍袖里,屈指刮了下她微红的颊侧,“皇后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总这么怕苦,你这体寒的毛病究竟几时能好。”
念阮被说得脸上愈发红了。她有体寒的毛病,冬日里总爱手脚冰凉,每每月事时皆疼得满头大汗,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算上从前两世了,独承雨露已久,肚子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上辈子她不想有他的孩子,自也没调养过,只因为月事腹痛喝过几个月的药,是令姒给她的方子,确也有用。而这辈子,她总觉得自己太小太小,还没做好做母亲的准备,又畏惧药苦,是故依旧不曾调养。
她扭捏着摇摇头:“……我不想生孩子呀,好疼的。”
又揽腰把他一抱,下巴枕在他胸前毛绒绒的狐裘领子上,眨巴着一双明眸楚楚可怜地望他:“陛下会疼念念的,对吗?”
嬴昭一怔。他只是心疼她体寒冬日里总要受那么多的苦,暂还未想到生孩子这一层上去。
但这事也是迟早要面对的,他是皇帝,不可能没有继承人,何况皇后无子,这一条罪名就足够大臣们把矛头纷纷指向她了。若是从宗室之中过继,终究是半路母子,倘若有朝一日他走在她前头,那新帝又会怎样对她呢?
可他亦舍不得她受苦,女子生孩子本就是过鬼门关,他父皇的妃嫔亦有不少是死于难产。即便宫中有最好的稳婆,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他只能含混应道,屈指拨了拨她微微凌乱的额发:“那也要先把身体调养好了。你月事时不是总爱疼吗?让姬恒也替你把把脉吧?”
念阮生动的眉眼霎时沉寂下去,抱着他的手霎时也收了回来,厌烦地背过身:“唔,怕是请不动仙人呢,等您养好了回宫再说吧。”
嬴昭薄唇微抿,欲言又止。他知她大概是在气他不顾她的感受把子嗣看得比她重要,可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若他只是一介平民,自可允她。可他却生在帝王家……
“顺其自然吧。”
他从身后拥住她,薄唇贴着她耳际温声安慰,“你我都还年轻,朕不急,你也暂时别去想这些事了。先把身体养好,不要为了躲避这事伤害自己的身体。好吗?”
念阮实则也有些愧疚,事关国家承继,这件事不是她能耍小性子的,何况她难道不想有他的孩子吗?只是……只是实在害怕罢了。
她微红着脸点点头,又有些赧然地问:“我……是不是太无理取闹了。”
两人正说着话,这时朱缨忽报令姒求见,俱都微微一怔。嬴昭骤然变了脸色:“她怎么上来的?”
她不是应该已和萧朗父子离京了吗?
这首阳山下密密麻麻皆是暗卫,为的就是确保他的安全。知他误会,朱缨忙解释道:“陛下,三娘子未上得山来,眼下还在山脚,自言有要事禀报。应是皇后堂姊,又是您亲封的女侍中,羽林们不敢隐瞒故而报了上来。若陛下不见,臣这就拒了去。”
“还是让她上来吧,兴许,是有什么大事。”
念阮抢先说道。联想到上一世的经历,她总觉得有事要发生。
帝后在观中暂住的客房里见了令姒。令姒着一身朱色骑装,鬓发散乱,绣鞋染血,浑身衣襟被荆棘划得无一块完好的布料,狼狈中不掩国色天姿。顾不得整理仪容,膝行上前娇喘微微:“陛下,皇后,民女有要事禀报!”
“我父萧朗反心已成,于今晨携我兄前往献陵,将调令陵卫逃回陕州作乱,请陛下、皇后圣裁!”
她一口气急促说完,双手叠放至额边,一拜触地,动作一气呵成、又急又响。
虽则萧朗逃走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令姒会来告密却是意料之外。嬴昭微微皱眉:“你怎么知道的?”
“回陛下,他们今晨本欲带我离开的,但民女自知家父此举犯下滔天罪孽,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他之主意,只能觍颜面圣!”
萧令姒把头埋得极低,朝着青石灰砖冒着寒气的地板,两痕脊背如梅枝轻颤,似乎恐惧到了极点。众人看不见的阴影里,一张脸却是沉如寒水。
念阮与嬴昭皆有些尴尬,又不便说早已知晓了,无言对视一眼,嬴昭道:“朕知晓了,会着人去瞧的。三娘子先下山吧。”
这个结果并非想象之中的要她留下,令姒微有迟疑,婉声谢了恩便要随折枝下去。她艰难地起身,却打了个趔趄两股战战重又瘫倒下去,绣鞋渗出血来,污了她所站的那方地板,淡然的眉宇微微皱起,轻声解释:“回陛下,臣女不是有意有污尊眼。请陛下恕罪。”
她态度始终不卑不亢,眼波宁和如月下轻波,没有恐惧也没有谄媚。嬴昭皱了皱眉,没说什么。念阮关怀地道:“堂姊这是怎么了?可是伤了脚?”
令姒摇头:“回殿下的话,臣女不会骑马步行上山,只是磨破了些许皮肤,没什么大碍。”
念阮眼睫微闪,终归回过味来,有些尴尬,却不动声色地唤了折枝上前,“你带三娘子下去吧。拿我的衣裙给她换上。再找父亲要些治疗创伤的药,女孩子的皮肤最是娇嫩,可别留下了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