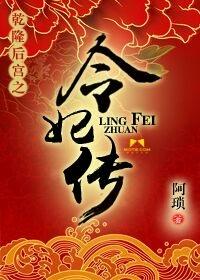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王爷掌心宠免费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梁孺心里面骂了声自己,手上却停不下来。
宋贵贵秀丽的模样在眼前来回盘旋,她捂上樱桃小口盈盈巧笑地样子,她眼泪汪汪噘嘴委屈地样子,活生生地把梁孺折磨得苦不堪言。
他觉得身体要爆炸了般。
勢裤渐渐地湿了起来,坚硬的东西来来回回不安分地闯来闯去,他却安抚不了,只好握着来来回回释放心中的窒闷。
极限之下,一下子卸下了所有力气。身体某处终于柔弱安静下来。
梁孺低低咒骂了声,飞速下床冲到净房重新冲洗干净。又把宋贵贵的帕子反复洗了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晾了起来。
梁孺心里后悔极了,帕子过了水,上面就再没有宋贵贵的味道了。原本他可以日日闻着这帕香入睡,可惜就怪了自己这么沉不住气,如今什么都泡汤了。
本来不多的困意一扫而光,梁孺干脆不睡了,开始给宋贵贵做招牌。
他卸下来一块长窄雅气的偏门匾,磨掉原来的字迹,开始琢磨着写些什么。
&ldo;贵饼。&rdo;
不好,不好,别人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朴素些就叫:&ldo;胡饼摊?&rdo;
不行,贵贵的饼摊怎么能这么没有特色。
梁孺在屋中转来转去,冥思苦想,时辰一个一个很快地过去,好的灵感却一个都没有闪现出来。
看来习文弄墨还是有好处的。
梁孺暗暗道。
他也不是不爱读书,只是……
哎,白折腾一晚毫无所获,梁孺把匾用块黑布遮了起来,翻身上床。
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另一头,宋贵贵可没有梁孺这么多心思,也没有他闲适,她可忙乎坏了。
宋贵贵一回家,就看见弟弟焦急不安地站在门外口等他。
这可不一般,弟弟这个时候一向是抓紧时间在屋中习书的。
今日肯定是家里出事了。
宋贵贵三步并两步快跑了过去,将饼摊放在院落一角,抹着额间细汗问道:&ldo;阿重,怎么了?&rdo;
&ldo;姐姐,可不好了,爹爹被坏人抓走了。娘跟他们拼命去了,咋么办啊!&rdo;
宋贵贵一听心里也慌了,强自镇定了下问:&ldo;先别急,仔细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