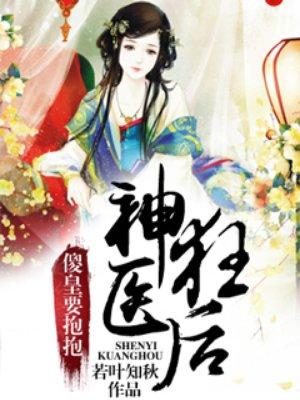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妖皇他不想做白莲txt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武枔柔:“沈城主说笑了,您正值壮年,何来的大限?我连山城如此行事,也不过是想求一条生路,迫不得已才暂时请沈城主屈居此地一段时日,等到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自当赔礼道歉,并恭敬将您送回戍庚城。”
“赔礼道歉就不必了。”沈略还是一身白袍,即便困于囹圄,但是没有受到任何苛待,就连住的地牢都干净整洁,除了不能自由行走之外,外表不见半点狼狈。
他悠悠起身,慢条斯理地整理了衣袍,转过来看向牢房外的武枔柔和林岩,“不过少城主有一句话沈某很是赞同,大家都不过是想求一条生路罢了,这是人之常情,旁人无法加以指责。”
林岩丝毫不隐藏自己的态度,嘲讽道:“沈城主既然有这等觉悟,又何苦将戍庚城半数百姓当作筹码,平白送去血祭?”
沈略却像是没听出林岩话中的意思,“林将军此言差矣,求生乃人之常情,但并非所有人都把生看得那么重要。”
“你自己想死,就可以拉着无辜人一起去死吗?即便你是城主,也没有这个权力!”
林岩平生最恨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更讨厌有人不把人命当回事。
“林岩!”武枔柔见气氛不对,赶忙拦住林岩,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好不容易把人安抚住,就听牢房里传来一阵低沉笑声。
那笑声很难形容,似乎是对林岩天真话语的不屑,又像是对某些事情的释然,听得武枔柔心中一个激灵。
沈略走动两步,距离两人更近,“两位是还没有看明白吗?现在的局势已经并非三族之间的争斗,而是生与死的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或许你们愿意忍受每千年一次的妖兽侵袭,在用少数生命换来的封印期里苟延残喘、恢复生机,然后再迎接下一次的灾难,我却不愿意。”
他说着,右手指甲轻轻一划左手手腕,浓烈的血腥味散发出来,鲜血顺着他的指尖流到地面上,竟是慢慢汇聚成一条细流,沿着地面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的凹槽缓缓流动。
“你在做什么?!”武枔柔大惊,赶忙命人打开牢门。
沈略却不愿意让人打断,只见他慢慢后退,直到脊背抵住墙璧,无形的灵力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这如献祭般的最后一击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是阻止了别人靠近。
武枔柔眼睁睁看着沈略脚下土地被鲜血染红,却不能前进分毫,看向沈略的眼神格外复杂,“你这是何必?”
沈略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白了下来,他嘴角一弯,笑意盈盈,“自然是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话音刚落,地牢外就有血光冲天而起。
林岩脸色突变:“是血煞阵!”说着,就往地牢外面跑。
武枔柔离开之前又看了沈略一眼,他的白衣上早就沾染上了斑斑血迹,看起来特别的狼狈。
“血煞阵的阵眼并非只有三个,即便没有连山城的半数百姓,我戍庚城也可以倾一城之力,独自完成这项创举。”
沈略说话时,眼中的阴郁被疯狂替代,看得武枔柔浑身发凉,知道他这是把整个戍庚成血祭了,沉默了许久,才从齿缝间挤出两个字:“疯子。”
迈步走出地牢,武枔柔还能听到沈略的笑声,她回过身,觉得刚才自己的同情狗屁不是。
她命令地牢下的守卫全部撤出来,“把门封死。”
这里她是再也不会踏足一步了。
出了地牢,就见城外无数道血光平地而起,在连山城上空汇聚成一团暗红色云团。
武枔柔一下就明白了,这些估计是城外那些戍庚城的士兵,或许沈略在来之前就给他们下过命令,看到什么信号后就一起血祭。
而且听沈略的意思,他们并不认为血祭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是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自己的牺牲也是为了后人安宁。
这种想法究竟是对是错,武枔柔不想评述,因为就沈略所说那些,除了极端些,别人根本无法指责什么,说到底都是各人的选择罢了。
她保护着武连山登上城墙,连山城百姓全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住,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安抚了。
林岩也在一侧守着,只不过目光正对着城外,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
无数戍庚成士兵的尸体堆叠在一起,密密麻麻挤满了城外的空地,看起来震撼且悲凉。
血色云团的范围一直在扩大,连山城众人还没有从刚才的动静中缓过神来,就见西北方森丘古地的所在也爆发出强烈的响动。
宗羽族地内,邢伋循着蛛丝马迹找到了位于妖皇殿地下的石室,却只发现了白力早已冷透的尸体。就在他上前仔细查看的时候,一道人影闪过,石室大门突然阖上,与此同时,白力身下血光大作,突破了石室的禁锢直冲天际。
妖族的第二个阵眼在宗羽族地内,负责启动它的人是鸿翼,只不过宗羽之主显然不准备自己送死,而是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好友。
刚才的人影明显就是鸿翼,邢伋抽出随身携带的金钊刀,用尽全力的一挥,石门应声破碎。
追出石室,他在妖皇殿外拦住了要逃走的鸿翼。
“人族与神族付出那么大代价来完成血煞阵还可以理解,我却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这么做?”
阵法针对的是森丘所有妖族,鸿翼没理由毁了自己的族地,还顺带灭了宗羽一脉所有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