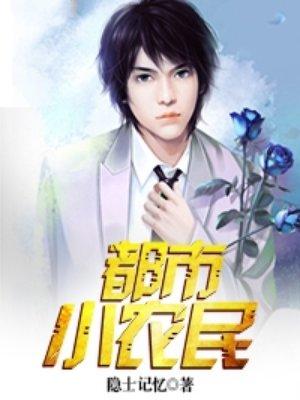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爱在梦里简谱 > 第159页(第1页)
第159页(第1页)
为了让船员们彼此间打碎隔阂、融洽相处,科林斯舰长每晚都会在中厅举行小型的“船长晚宴”,每个人必须参加。郁臻十分羡慕杜彧,因为是小孩,可以在房间里安心睡觉和看电影;而他必须跟一群陌生人托着腮坐满40分钟。以至于他无聊得叼了根吸管,对杯子吹空气。强行聚会对除他以外的船员是有效果的,他眼见这两日船上的气氛变得热络。那几位科研人员很快打成一片,每天为长波扫描到的新数据而兴奋,坐在一起对cielt45的地表重力和可能存在的生态圈进行热烈讨论和分析。郁臻听了一耳朵,以他的知识储备自然没法参与话题,其实他从小就不热爱学习,只是擅长记住考点,所以成绩过得去;真要论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他……很惭愧,他甚至从没思考过自己有一天能离开地球。杜彧的幻想一向有迹可循,或许修斯特·普兰维林真的做过那样的梦;来自遥远未知星系的神,冥冥之中为他指引了一条道路,让他站在人类的顶端,有朝一日深入太空,寻找另一颗太阳下诞生的文明。船上的科学家们显然不相信神衹托梦一说,他们只想知道新大陆有什么石头和植物,氧气含量和气候如何,至于文明,那是考古学家的工作。郁臻咬住吸管,感受被变形的塑料褶皱刮着舌头,轻微刺痛,他看向角落的一张圆桌——此行唯一的考古学家坐在那里。她叫何安黎,身处探险队伍,同伴是两名信奉主的探险队员;也只有他们对巫马讲述的故事兴趣浓厚,时不时能见到他们和巫马聊天。何安黎是18名船员里最吸睛的人,她年轻漂亮、爱笑,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喜欢穿露肩的针织衫,四天内拒绝了五个男人的搭讪。郁臻无所事事时,一大爱好便是观察人,他首先选择的对象是何安黎,经过三天的粗浅交谈,他收集到以下信息:何安黎29岁,拥有城市考古学和符号学双博士学位,会说四种语言,两种失传古语言;收到普兰维林公司的邀请邮件之前,她一直和化学教授未婚夫在巴黎研究和寻找尼古拉·弗拉梅尔的魔法石,他们相信那不止是传说,而是某种未被破译的神秘物质。原本他们都收到了邀请,但她未婚夫的体能训练最终未达标,她选择果断登船,他留在地球,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为什么郁臻会观察她呢,除了她亮眼,还因为她对巫马的态度与众不同。巫马长着杜彧的脸,郁臻格外关注他。说何安黎对其态度不同,是因为她会和巫马聊天,并且热衷于和他聊天。船上大部分人对巫马的态度是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助理,当然即便不招手,巫马也会自觉提供周到的服务,毕竟这是他的工作和责任之一;但何安黎不那么想,她不使唤他,还主动跟这名仿生人交流。郁臻听过他们的对话内容,什么舒伯特的a大调五重奏谐谑曲、维也纳分离派的装饰运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玫瑰线;他听得昏昏欲睡,作为缺乏表达欲的人,他对艺术的鉴赏力尤为不敏。哎,既没有好玩的,更谈不上好吃的,太空航行生活真是一个无趣至极的梦。郁臻坐满40分钟,吐掉吸管走人了,只有欺负孩子能给他带来些许快乐。沙丘号设施完备,有电影放映厅、射击训练场和各位运动器材。走出中厅,舱门自动感应开启;郁臻去放映室找杜彧,那小孩正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着银幕目不转睛。幼年杜彧喜欢看1950年前后的老掉牙动画片,他已经跟着看了一遍《白雪公主》和《通烟囱工人与牧羊女》,现在杜彧在看1958年东映动画制作的《白蛇传》,很复古。郁臻走近,两手蒙住小孩的眼睛,“答题时间,请回答——”杜彧拍打他的手背,稚嫩的童音道:“你很讨厌,二十多岁的人了,幼不幼稚啊。”郁臻闭嘴,他改变主意了。他翻过沙发转到杜彧面前,手握住小孩荡着的细脚腕,然后一提一举,小崽子就像只被倒吊放血的猪仔,拎在他手里。“啊哇啊哇——”小孩突然间被倒转头朝下,张牙舞爪地乱打,反手揪他的裤腿。郁臻:“好,现在回答问题,答对了放你下来。”“不要不要!”郁臻狠力抖了抖手,把孩子颠得直晕。“回答问题,我是谁?”杜彧:“是爸爸!我最爱爸爸了!”郁臻听到正确回答,想的是:这孩子也太没意思了吧……“不对,重想。”他换了答案。杜彧哇哇大叫:“你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心肝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