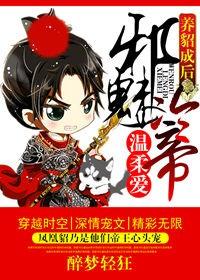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软萌反派穿书txt > 第87章(第1页)
第87章(第1页)
阮筱朦耐着性子坐下,看见离自己最近的那个笼子里,两名男子身材悬殊,一个黝黑魁梧,一个清瘦单薄。俩人都是衣衫褴褛,脸上弄得脏兮兮的,看不清面目。
看客自然都押壮汉会赢,角斗刚一开始,就有人口出恶语,诅咒另一方去死。
到底是一条人命,阮筱朦忍不住默默地为那人捏了把汗,估摸着,自己随时会看见他血溅当场。
三对笼中人像困兽一样,彼此扭打、厮咬、缠斗,在这场以命相搏的游戏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谁都输不起。
很快,那人便落了下风,他的对手壮得像头牛,无论是体格或力量,他都占尽了劣势。
他挨了一拳,鼻子和嘴都在流血,若非脸上尽是黑灰,想必也是又青又肿;他的手臂被狠狠地绞了一下,阮筱朦看见他痛苦的神情,都能想象骨骼作响的声音;他的腹部又挨了一脚,猛地向后飞出去,重重地撞在生铁铸成的笼子上……
阮筱朦简直不忍心再看下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意志真的是坚韧不拔。这人除了毅力不凡,也实在没什么可称赞的地方,他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人在笼子上撞得太狠,半天爬不起来,壮汉从笼子的另一头缓缓靠近,像一头准备咬断人脖子的狼,马上结束最后的战斗。
那人一直没有起身,他拔下头上束发的木簪,一根、一根、一根地敲击着笼子的铁栏杆。因为距离太远,木簪敲出的声音也不够清脆,所以,阮筱朦听不清。可是,她瞪大了眼睛,已经猜出了他的用意。
木簪敲击的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以为他疯了,以为这是他死前神智不清的发泄。
如果,阮筱朦不曾亲身经历过摄魂术,她大概也会这样以为。
难怪,她总觉得这人的身形举止似曾相识,难怪,楚蓦会叫楚星带她来这里。
在木簪不断敲击铁笼的声响中,壮汉停止了攻击,像是饿狼突然迷失了方向。就在他止步不前之际,那人喘·息着站了起来,冲过去,将手中的木簪狠狠地插·进了壮汉的脖颈之间。
牛一样的汉子倒了下去,脖子上鲜血喷溅。他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
这无疑是爆出个冷门,输了钱的看客站起身来,指着浑身是伤却还活着的人咒骂不止。也有少数人兴致勃勃,直呼有趣。
“他是苏亭之?”阮筱朦其实已经肯定,却难以置信,“苏亭之是大成余党?”
“是。大人说,当日苏亭之竟敢在郡主府中使用摄魂术,此事因他而起,他答应过郡主,要帮您将人追回来。现在,大人有了此人下落,命我带郡主来看看。郡主无需亲自动手,苏亭之既到了这样的地方,左右是没有活路的。”
阮筱朦知道,今上登基以来,别的建树没有,在清除大成遗党的事上,却向来是铁血手腕,斩草除根。
曾经那个弹着《长相思》,清隽绝艳的公子,竟已落泊到这步田地。阮筱朦至今记得,初遇时他的眼神,眸光潋滟,却空洞得让人心惊。他抚琴邀宠,稀罕的不是她的人,而是她的命。
笼门被打开,壮汉的尸体被人抬了下去,笼子里,很快又重新送进一个人来。这是车轮战,除非连胜三场者,今日才能歇着,明日再战。楚星说的没错,人到了这里,一条命活过今日,未必活得过明日,迟早都是死。
新进的这人身材还算匀称,神情却猥琐,让人看着就不舒服。他见苏亭之经过一轮角斗,虽然活了下来,却已经伤重成这样,料定不是自己的对手。他这场算是捡漏,脸上浮起一丝轻快,眼睛不怀好意地往苏亭之的身上瞟。
苏亭之那身衣衫本就破烂不堪,打了一架,被几番撕扯,更是衣不蔽体。他脸上抹了黑灰,看不出容貌,身上的肌肤却白皙夺目。那猥琐汉子几乎要流口水,搓一搓手,蹭上前去,也不知是想打架,还是想揩油。
苏亭之对这不假掩饰的垂涎目光非常厌恶,他一手捂着腹部痛处,一手撑着地,往后缩了缩。
方才那人虽狠,至少不让人恶心,而现在的对手,苏亭之若被他碰一碰都会起鸡皮疙瘩。他大概决定先下手为强,染血的手握着染血的木簪,又开始敲击栏杆。
然而,摄魂术虽然厉害,却是门极其消耗自身内力的功夫。以阮筱朦对苏亭之的了解,他学摄魂术根基尚浅,内力本就不算雄厚。他待在这里,受尽虐待,想必身体早就吃不消了,何况眼下,还受了伤。
果然,苏亭之在虚弱的状态下连接使用摄魂术,这一次,他没敲几下,便停了下来,咬紧的牙关一松,喷出口血来。
猥琐汉子刚恍惚了一会儿,声响一停,他很快恢复了神智。他意识到这小子有两下子,生怕稍作耽搁,又会着了他的道。
那汉子迅猛地冲过来,狠狠掐住了苏亭之的脖子……
抹了黑灰的脸看不出泛青憋紫的转变,苏亭之茫然无神地睁着那双漂亮的桃花眼,像悲伤,像解脱,像绝望,绝望得让人心头发颤。
就在他等待着死亡降临的时候,掐着他的那双手,突然松开了。
猥琐汉子直挺挺地倒下去,颈上汩汩地冒着血,那里,插着一支银雨袖镖。
苏亭之抱着自己的脖子又咳又喘,难以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他顺着那汉子中镖的方向,转头望去,远远的看台上,站着一道清丽耀眼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