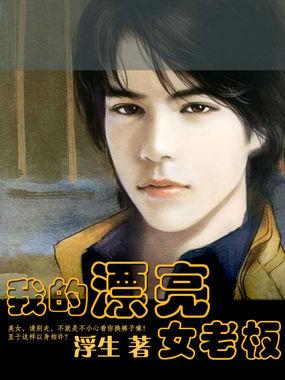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在年代文里吃瓜乐文 > 第二百三十三章 西南列车(第1页)
第二百三十三章 西南列车(第1页)
前往西南的火车在铁轨上飞驰而过,留下一串轰隆隆的汽笛鸣声和列车轮对下飞扬的尘土,首都的景色飞驰而过,远方是一片遥望无垠的浩荡平原。
此次带队的医疗队长是她们复合班的学科老师,是位高冷寡言的中年女教授。
通常她穿着医院白大褂匆匆赶来上课,一打下课铃绝不拖堂,抱起课本直接飞快离去。
同学们想追上去询问课上没有理解的知识点时,往往刚站起来,就只能望见她的衣摆一角迅速消失在门外,眨眼间就没了人影。
在校老师大多是医院医师,以往工农兵大学的教学任务不重,治病授业两手抓。可现在恢复高考,学校课程安排一下紧凑起来,导致他们成天连轴转。
云父云母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不教复合班,而是普通班级,同样是上了课就走,所以即便在一个学校,也不能天天碰面。
除了云苓,同行的还有她们班长乔瑞雪。
见到她,好像一点都不意外:“昨天我妈告诉我队里突然加了个学生,我一猜,不是你就是齐弦春。”
云苓眨眨眼,有些懵:“你妈妈?”
乔瑞雪躺在她对面的中铺上,倒有些惊讶:“你不知道?”
“我没有随意打探别人隐私的癖好……”
班长笑了声:“你还真是山人隐居于闹市,两耳不闻窗外事。”随后大拇指朝着隔壁右边方向的包厢隔空点了两下,“带队的那位,就我妈。”
云苓察觉出对方话语里的冷淡,依旧没有探究之意,适当地露出一点吃惊:“付桢教授是你母亲?”
乔瑞雪厚重的眼镜片下流露出一丝讽刺的意味,轻声自嘲:“其他人知道时,大概也是你这副表情吧?不过也正常,谁家母女像我们这样?跟陌生人似的。”
未等回答,她又开始自言自语:“虽然我跟你接触不多,但齐弦春跟你关系还挺好,他人不错,想必你也信得过。”
云苓抱着刚打算翻开的书,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班长不会是要把她当作情感树洞吧?
果不其然,乔瑞雪不急不缓地开始自说自话:“你都不知道,班里人怎么说我的。”
“怎么说的?”
云苓只好把书重新放回挎包里,瞥见刚要进来的男人,不好意思地递了个眼神,岳鸿进同志便拎着暖水壶去打水了。
“有次我妈上完课就走了,那节课间我去上厕所,回来时听见他们议论我俩的关系,说是在学校装不认识都是为了避嫌,实际上,能当上班长是因为我走了后门。”
这件事云苓不太清楚,因为她经常缺课,否则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实验,学校那边也是提前过了明路,但前提是她可以通过所有年级的期末考试。
正是因为科科满分的答卷,甚至面试时临场作答都是完美的流利规范,她在大学才能明目张胆地享受极高自由度。
“他们居然还拿我跟你比,笑话,一群怂蛋,自己追不上就想把我当枪使,当谁是傻子呢?”
云苓的本事全校谁不知道,即使学校隐匿了教材编撰者的姓名,但有本事有门路的人还是能打听出来的,乔瑞雪就是其中之一。
更何况大一新生以全科满分的成绩通过八年的期末考试,早已在全校一鸣惊人了。
一开始她是抱着不服输的心态想比量比量的,因为同样是医学世家出身,高考比不过人家省状元就算了,那从小学习的专业还能输嘛?
起初越挫越勇,但后来被打击的次数多了,也逐渐学会了坦然面对。
现在她的目标已经换成了班级第二的齐弦春。
云苓蹙眉听她讲述班里私下的嚼耳根,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乔瑞雪愈发滔滔不绝:“你也看到了我妈那样,我就奇了个怪了,我从小到大没有享受母亲的一丝温情,却还得因为她的母亲身份,别人就否定了我的一切努力,凭什么?这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