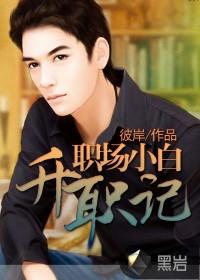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师尊在上免费阅读 > 第44页(第1页)
第44页(第1页)
但二师兄是不知晓这些的,因而也未料到,规矩(二)“我也赌宵师兄……”人群里有人弱弱地附和。“又有个上赶着当冤大头的,赌资赌资,别光说不下注。”陈落庭从怀里拿出一沓银票,周遭人眼都直了。“乖乖,你这小子,藏得挺深啊。”这银票当初是陈沅沅给的,本是不屑,如今倒还有些用处。陈落庭这大注一下,蠢蠢欲动或摇摆不定之人便多了。再观战局,宵随意似乎气定神闲,唯一剩下的来神峰弟子倒是落了一滴汗。人群观察入微,这简简单单一滴汗,竟让不少人反水,改押宵随意胜。二师兄风刃一道接一道,丝毫不留情面。桌底下的六条腿,来回周旋,快得已成虚影。来不及接下的风刃,便从缝隙中窜出,扑向众人,众人对这状况习以为常,有序避让,未伤及分毫。风刃愈发凌厉,宵随意想要再装得若无其事,已是不可能。他双手握住木桌边沿,借了支撑,勉力让自己站稳。另一位局中弟子见此情景,不管三七二十一,指责宵随意违反规矩。他这一分神,脚下明显不稳。宵随意可不想当正人君子,瞅准时机,连续朝那人投去几道风刃。那人轻而易举出局,人群哗然。可宵随意与二师兄却未停歇,二人间的你来我往已不仅仅局限于风刃,而是以脚力相互抗衡,灵力更是倾注其上。二师兄亦双手握住桌沿,那张方桌已渐渐脱离地面,成了二人掌中互相制衡之物。掌中灵力沿着桌面传递,桌下又电光火石,木桌就是件俗物,哪能承受得住,顷刻便化作碎屑。附于其上的灵力无所依存,骤然四散。众人以为,这灵力再是厉害,像狂风一般吹个来回,也便能消湮了。岂料宵随意与二师兄都拿出了真本事,二人汹涌灵力哪是狂风能比拟,分明是海中吞舟噬人的巨浪,巨浪冲上了屋顶,屋顶……飞了!——柳权贞翘着二郎腿坐在无念殿前堂太师椅上,宵随意跪在他跟前,深埋着头。“长本事了,吃顿晚膳能将人家屋顶都掀了。”“师尊,徒儿知错。”柳权贞起身围着他转了一圈,站定于其身后,不说话。宵随意有些慌张,他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忽听师尊道:“可有受伤?”宵随意没想到师尊会这么问,责怪也好,体罚也罢,他觉得师尊不会有所顾念,也做好了承受的准备。哪知师尊总是与常人思维不同。“还好。”他保留了伤情。“那便是有伤在身了。”柳权贞一眼便瞧出来了,徒儿双腿微微发颤,俨然是施力过度。“近日你可要荣登玉琼山话题榜疏离宵随意哪有什么亲眷家人,即便有,也决计不想见了。前世,他倒是回去祭拜过娘亲,也愤愤地想去找姨娘和生父寻仇。但因果轮回,他回到那薄情生父的居所时,得知宅子不久前半夜失了大火,宅子里无一人生还。老天爷替他报了仇。这一世,那些令他痛苦的恶人,就让命运去主持公道吧。“如今我唯一的亲人便是师尊了。”他道。柳权贞站在门槛前看着堂前树,明明是盛夏烈日,该是枝繁叶茂的季节,却仍有败叶落了一地。他料想宵随意会这么答,便道:“那你中秋当日随其他师兄弟下山去玩玩,你这个年纪,总不能一直闷在我身边,该多交些朋友。”宵随意觉得此话太过语重心长,甚至都不像师尊了。想起之前陈落庭之事,他不敢保证师尊这话是由衷而出。他若是时常与朋友厮混在一起,怕师尊到时又是另一番说辞了。“师尊为何不与我一道去呢,我与师兄弟们并不熟络,一起去了山下,也玩不痛快。”“为师有要事在身,不便一同前往。”师尊近来看起来很闲,宵随意想不出他能有什么要事。“那我便同师尊一起去办要事,不去山下玩了。”柳权贞却厉声道:“这事只能为师一人去办,不便有人陪同。你如今也不小了,别老是师尊长师尊短的。”宵随意一愣,未料到对方竟然生气了。师尊的眉宇已经拱起来,非常少见的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心头溢出一丝惶恐,连忙哄慰:“是我逾矩了,我不缠着师尊了,师尊想忙什么便去忙吧,我绝不打扰。”或许是自己将这师徒关系想得太亲昵了,到底是要保持些距离的。柳权贞捏了捏眉角,他看起来并未因宵随意讨好的话语而心情愉悦。过了须臾道:“为师这几日钻研术法,遇瓶颈不得解,心情不甚好,方才未收敛好情绪,你莫要东想西想。”说罢未留给宵随意反应的时机,径直走开了。饶是宵随意再木讷,也发觉到了师尊的不对劲。比起往日,他更加喜怒无常了。以往师尊没少在术法上遇到困难,却没有心情差到像今日这般。他总能找到排遣的途径,或喝喝酒,或耍耍剑,或与自己说道说道其中不开窍之处,灵感便来了。眼下,酒或许喝着,那身自白日到晚上自带的酒气从未散过。剑却是不耍了,追魂快成摆设,更别谈与自己沟通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