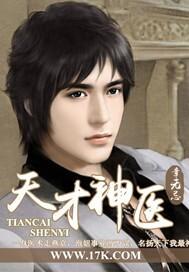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明月照我心原著免费阅读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他借着芙蕖的搀扶,冷静的站起身。栾深问:“上我的车?”谢慈一句不必,抓着芙蕖的肩膀,无比利落的飞身上马。栾深见状才松了口气。芙蕖至此沉默了一路,再也没敢在马背上胡来。回了谢府中,下马后,芙蕖身后按了按谢慈的前胸腹部,问:“你伤着没有?”谢慈:“你是兔子吗,蹬腿往人心窝子里踹,我身上怎么没被你捣出一个洞?”芙蕖:“等回屋我给你瞧一瞧。”谢慈松了手,放她自便,迎了栾深,往书房里去。芙蕖原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这二位的情分还真是不一般。谢慈的书房可不是谁人都能进得了。芙蕖原地感慨片刻,想到了自己的烦心事,不免忧愁,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可回头一想。即使她能赶在谢慈前面弄清真相,赶到苏府,也未必能把东西搞到手。苏府可不会买她的面子。她也没有谢慈那疯癫的手段逼苏府就范。如今,东西已不在苏府,不知姚氏得了这个消息,该作何反应。芙蕖坐在院中的梧桐树下,头顶的叶子已经开始飘黄,今年的乌鸦幼崽已经羽翼丰满,满院子里叽叽喳喳格外活泼。消息放出去,姚氏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她的目的如果真是那解蛊的方法,她一定不会任由自己十数年的精力白费掉,她会想尽办法,再从谢慈身上下手。芙蕖不相信谢慈在苏府当场就烧掉了解蛊之法。她琢磨着,找个合适的时机,约苏慎浓见一面。也不知苏府现在的情况如何。苏戎桂必定不会善罢甘休,谢慈还有的麻烦。芙蕖觉得自己可能是受到了刺激,脑子里东一头西一头,想来想去,确实乱七八糟的事,一点调理也没有,也完全静不下心来,一闭上眼,就是方才路上摔下马时,躺在谢慈怀里的光景。隔着谢慈身上那薄薄的一层衣料,她控制不住的去回想那心脏的跳动。两个人的心跳像是形成了共鸣,在那短暂的时间里,震耳欲聋,令芙蕖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响,心里也拉成了一片空白。像酒的味道,又苦涩又上瘾。谢慈在书房脱去了外罩衫,与栾深相对而坐,“你想政治吏部,当下就有一件事可以给你当做筏子。”栾深立即意会:“白合存。”谢慈:“白合存的升迁其中必然有猫腻,礼部侍郎与此也有脱不开关系。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根藤上牵一串。到时候肯定有热闹看。”他一杯热茶倒进口中,激起了一阵咳嗽,像是从肺中灌出来的,时断时续,一直停不下来。栾深赶紧倾身再给他续了杯茶。谢慈摆手示意不能再喝了。栾深道:“一个女人能带着你翻下马,堂堂次辅大人,你真让我开了眼……没事吧?”谢慈抚住胸口,闷闷地舒了口气:“无碍。”栾深侧头朝外面看了一眼,说:“人家姑娘喜欢你,一往情深,你何必非要把人往外推呢?”谢慈稍作喘息,平复下来,道:“世人都道我疯疯癫癫不成人形,其实她才是魔怔的那个。她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沉沉浮浮,性格都长歪了,一心挂在我身上,连自己是谁都拎不清。”栾深为人机敏,很能理解谢慈的深意,说:“你倒是用心良苦,那你希望她怎么做呢?”谢慈道:“我从未把她当成我手里的一把刀,是她自己。人这一辈子,两件事情不能忘——不能忘了自己是谁,不能忘了自己要干什么。她什么时候想通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放心。”他这一番话其实没表现出多少愁意,但仔细回味起来,不难察觉到满腔的艰涩。栾深摇了摇头,劝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感情面前是讲不通道理的,你是个克己禁欲的圣人,可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和你一样。”芙蕖迈出的脚步缓缓退了回来。她就站在一窗之隔的外面,他们谈话的声音清晰的传进了她的耳朵里,以她的听觉,一字不落。芙蕖背靠着漆红的柱子,仰头望着湛蓝的天。——不能忘了自己是谁。——不能忘了自己要干什么。她是谁?她是六岁那年被抛弃的白家女。她是六岁那年被卖入谢府饱受折磨,差点死在到刽子手刀下的小废物。她是六岁那年被谢慈救下,此后便一直呆在他身边的一条小尾巴。那一年的塘前街、鹿梨浆,像是一道天堑,隔开了两个小女孩的命运。她们一个名叫小麦,一个名叫芙蕖。小麦的生命是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声啼哭开始。芙蕖的命则是从见到谢慈的那一刻开始。一想到这个问题,铺天盖地的阴霾和绝望兜头向芙蕖压了下来。他好了不起啊,他是神,他的心胸能装下广阔的山河天地,也能安然的容纳一座自己的坟墓。但是芙蕖不行。她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九曲迂回的牛角尖,一旦绕进去了,便再难出来。至于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她什么也不想做,万事万物皆乏味至极,她宁愿守在牛角尖里,困死自己的一辈子。世上根本没有能令她开心的东西。她的面前横亘着一座永远也越不过去的山,有关谢慈的点点滴滴,像从土壤中蜿蜒而出的藤蔓,死死的缠绕着她,令她寸步难行。她是守在山中的信徒,生于斯,长于斯,假如某天一场山火要将这所有的一切燃烧殆尽,那么她一定会以身殉葬。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行尸走肉的模样。而她自己却浑然不知,甘之如饴。她身处在一片混沌中,难以自拔,可谢慈却始终清醒,他不曾有一日忘记自己是谁,也不曾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与栾深只浅浅的闲聊了这几句,马上又回归正题,说:“白合存的夫人姚氏,身份特殊,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靶子。你准备何时动手,我助你一臂之力。”栾深倒不想他那么积极,他叹息道:“可惜了白合存,我看他是个老实人。”谢慈冷然道:“娶妻不贤,心智不坚,这样的人在向乡下庄稼地里赖一辈子,也没人去捏他的错处,可他偏偏要往燕京城里蹚这一谈滩浑水,身居高位,无能就是罪。”栾深道:“我喜欢听你说话,因为你总是有说不完的道理,可以在任何时候提醒我理智行事……对了,白府和苏府之间的关系,你已经查出结果了?”谢慈不遮不掩的回答:“查到了,没什么意思的家长里短,姚氏,也就是南秦的公主,年轻的时候,给她未婚夫头上扣了顶绿帽子,不料被她小姑子的打击报复,整治了个半死。她那小姑子冒犯皇室最后也没落着好,被南秦献上了我们大燕朝,赏进了苏府,当了一房小妾。那妾留下一个种,就是苏秋高……”栾深听得皱眉,说来说去,果真净是些家长里短的故事,他忍不住问道:“等等,难道其中就没有什么阴谋?”谢慈一顿,敞亮答道:“阴谋?那还真没有!”他只字不提有关蛊毒的内情。此事谢慈是打定了主意瞒着所有人,连驸马也不能告诉。芙蕖对如何整治无能之辈没什么兴趣,她回到自己院中给,提笔就写了一封信,约见苏慎浓,亲自出门托人递进了苏府。想着苏慎浓正忙着关照父亲和兄长的身体,此刻必焦头烂额,顾不上其他,芙蕖刻意将话说的委婉诚恳。本已打算过些日子再议此事,不料,帮她递信的小厮出门传话,说苏慎浓约她半个时辰后,在春耕茶亭见面。芙蕖喜出望外,心里搁着谨慎,人却没有走远,一直守在苏府的外围,直到半个时辰后,亲眼见到苏慎浓出府,才一路跟在她身后,安全互送她到春耕茶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