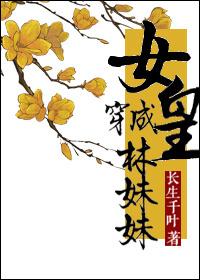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蓝色地狱火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我们慢慢往北开,时速不会超过五十英里。凯迪拉克的油箱几乎是满的,可能足够带我跑个三百或三百五十英里,在这种慢速行驶的状况下,跑的里程甚至可能更多。加速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像这种已经有八年车龄的八汽缸引擎,如果猛踩油门的话,那消耗汽油的速度会比咖啡从咖啡壶倒出来的速度还快,但如果维持慢速运转,就可以撑多一点里程数,甚至有可能多达四百英里,或许可以往西跑到孟菲斯市。
车子一直开着,那辆脏兮兮的红色卡车因为够大,即使它在我前方三百码也是个显著目标。它绕过亚特兰大市的南边往左转,打算穿越乡间往西走,看来伪钞流通的理论是正确的。借着通过交流道的机会,我把速度放慢,让自己离它远一点,因为我不希望司机怀疑自己遭到跟踪。但是看他变换车道的方式,可以得知他不是一个常常看后照镜的家伙,于是我又跟得稍微近一点。
红色卡车一直开着,我跟它保持八辆车的距离。时间也一点一滴过去,下午的时间已经耗尽,渐渐接近傍晚,我一边开车一边吃棒棒糖跟喝水充当晚餐。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收音机,那收音机是日本制的花稍货,一定是修车厂那家伙换上去的,可能坏掉了。真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宾利的车窗,查莉拿回车子后如果发现车窗变成黑色,会不会昏倒?但这不该是她最需要烦恼的事。我们一路继续往前开。
我们开了几乎四百英里,八小时的车程,出了乔治亚州之后穿越亚拉巴马州,进入密西西比州的东北角,天色已经是一片漆黑。秋阳在我们前方下沉,大家纷纷把车灯打开,虽然我们在黑暗的天色中只开了几个小时,但这一段路程却让我觉得好像一辈子那么久。接着,在午夜之际,红色卡车放慢速度,我发现它在我前方半英里处开进一个卡车休息站──这鬼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它靠近一个叫做摩托的城镇,大概离田纳西州的州界六十英里,离孟菲斯市七十英里。我跟着卡车开进停车场,停得离它远远的。
我看见司机走下车,是个粗壮的高个儿,虎背熊腰,脖子也粗,一头黑发的三十几岁男人,两只手臂长的像猿猴似的。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克林纳的儿子,那个冷血的疯子。我盯着他,他下车后站在车子旁边,在黑暗中伸懒腰、打呵欠。我一边瞪着他,一边想象上礼拜四晚上他在仓库门口手舞足蹈的模样。
※※※
克林纳小子锁上卡车后,漫步走向休息站,我等了一段时间才跟着他进去。我猜他会直接去厕所,所以我在霓虹灯下的书报摊闲晃,一边盯着大门。他走出来,慢慢步向用餐区,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再度伸展身体,拿起菜单时那副慢条斯理的模样一看就是个纨袴子弟。他来这里享用迟来的晚餐,我猜大概要花个二十五分钟,或许半小时的时间。
我回到停车场去,想要闯进红色卡车一探究竟,却发现没有可乘之机,一点机会也没有,因为到处都有人走动,两个公路巡警也在那里闲荡着,整个停车场都笼罩在灯光之下。等一下才有机会。
我走回休息站,钻进一座电话亭,拨电话回马格瑞夫警局,芬雷马上就把电话接起来。我听到他那低沉而带着哈佛味的声音,他就坐在电话旁边等我的消息。
「你在哪儿啊?」他说。
「离孟菲斯市不远。」我说,「我看到一辆卡车上货,就一路紧跟着它,有机会我就上车去看他们搞什么鬼。司机是克林纳的儿子。」
「好。」他说,「皮卡那边也有消息。萝丝可现在很安全,八成睡熟了。他说她要对你传答爱意。」
「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说一声,我也爱她。」我说,「保重啊,哈佛佬。」
「你自己也要保重。」他说完就把电话挂掉。
我漫步走回凯迪拉克,坐在车上等,半小时后克林纳小子出来了,我看着他走回红色卡车。他用手背擦着嘴巴,看来似乎好好吃了一顿晚餐,时间实在拖了很久。他走出我的视线一分钟后,卡车从我身边经过,从出口的路开出去,但是那小子并没有回高速公路,他左转开进高速公路旁的辅助道路,绕到一间汽车旅馆,看来是要去过夜。
他直接开到汽车旅馆的一排套房前,把红色卡车停在倒数第二个房间前面,笼罩在柱上大灯的光芒下。他下来后把车锁上,从口袋里掏钥匙出来开房门,进去后把门关上,接着开灯关窗。他早就拿到钥匙了──他没去旅馆办公室,所以一定是在休息站用餐时预约了房间,付钱后就拿到了钥匙,因而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才出来。
这样倒是给了我一个难题:我必须进去那辆卡车,我需要取得证据,并且确定办案方向是对的,马上就得确定,距离礼拜天只剩四十八小时了,一堆事情要在礼拜天之前完成。所以,就算那辆卡车被柱子上的灯光笼罩,而且那丧心病狂的克林纳小子就在十英尺之外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我还是要闯进去一探究竟──虽然这件事可能会要了我的命。我必须等到有机会再做,等到那小子睡熟了,以免被我行动的各种怪声吵醒。
我等了半小时,实在不能再等。于是我发动老凯迪拉克,在一片寂静中开动它,汽车内燃机的推杆与活塞都开始活动,引擎发出轰隆隆的噪音。我把车子紧靠着红色卡车停下,车头正对着那小子的房门口,然后从前座的乘客座位下车,站着不动,倾听片刻还是没有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