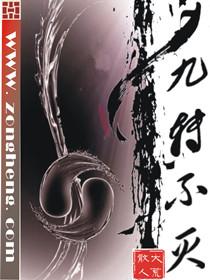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月光沉没by初禾推文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荆寒屿又道。
雁椿瞥荆寒屿,荆寒屿半侧着,少年的轮廓在正午的阳光下有一圈金芒,脖子上有大片阴影,显出与年龄、真实不服的力量感。
“哦哦,那我走了啊。”
李华拿上饭卡就溜。
正是长身体时,即便是以学习为重的实验班,吃饭也是很积极的。
这时班上已经没剩几个人了,荆寒屿再次转向雁椿。
“雁寒屿。”
少年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像粗粝的风袭来。
雁椿虽有心理准备,脸颊还是不由得烫了起来。
他还记得小时候荆寒屿气呼呼地给他说,不能随便改成别人的名字。
现在他偷偷改,正主来找他算账了。
“雁寒屿。”
荆寒屿的声音早已褪去少年的喑哑,变得低沉悦耳,两个声音像是从时间的不同方向奔涌而来,带着截然不同的情绪,在雁椿的听觉里撞击。
雁椿记得17岁的自己在听见荆寒屿这么叫他时,尴尬地大笑几声:“荆同学啊,你好。”
荆寒屿皱着眉,“雁椿,为什么改我的名字?”
“啊?”明知戏已经演不下去了,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继续挣扎,“什么雁椿?”
荆寒屿沉默而失望地看了他一会儿,转身离开。
不成熟的小孩才会干这样不成熟的事。
29岁的雁椿长吸一口气,转过来和荆寒屿对视,语气有种波澜不惊的从容,“荆先生还记得那件事。”
电梯发出提醒音,催促关门,荆寒屿的眼神一瞬间涨满失望,几乎和雁椿记忆中16岁的少年重叠。
可他在失望什么呢?
16岁的荆寒屿因为他装不认识失望,现在他又没有装不认识。
电梯就这么悬着,荆寒屿的手还压在梯门上。
雁椿不得不问:“还有什么事吗?”
“进来。”
“可我有东西忘了。”
“我等着。”
成年人不会不给彼此留余地,荆寒屿此时简直像个不讲道理的小孩。
雁椿的冷静在此刻绷出一道裂纹,他甚至没有跑回宴会厅做做样子,便擦过荆寒屿的肩膀,走进电梯,余光里,荆寒屿的手背血管和青筋一并鼓起。
谁按电梯门会这样用力呢?
荆寒屿松手,梯门像耐心告罄似的匆匆合上,映出两人模糊的影子。
雁椿心脏跳得很快,他嗅到一丝酒气,荆寒屿喝过酒,是醉了吗?
酒店外有个露天停车场,两人的车都在那里。
饮酒的人开不了车,走到停车场已经是该分开的时刻,雁椿先开口,“需要我帮你叫代驾吗?”
荆寒屿回头,眼神在夜色下比平时更加浓重深沉,好像藏着很多雁椿该明白,却又不明白的东西。
“不。”
荆寒屿说。
“那通知你的助理还是别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