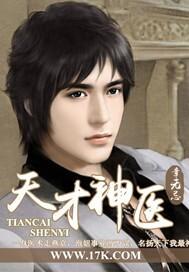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归离原的圆盘在哪 > 第46章(第2页)
第46章(第2页)
过了片刻,她侧首对一直站在暗处的墨烆道:&ldo;传令穆国分座,让他们寻个合适的机会,替那位含回公子另外找个清静些的住处。&rdo;
&ldo;是。&rdo;墨烆道,&ldo;卫垣那边可要继续监视?&rdo;
&ldo;不必了。&rdo;子娆道,&ldo;撤去所有部属,只留意太子御的动静,若他和卫垣往来过密,即刻报与我知道。&rdo;说着飘然转身,罗袖淡扬,金丝玉帛悄无声息地落入深冷的湖水,转瞬便沉没波心,连一丝涟漪也未曾遗留。
精舍中灯仍亮着,子娆沿无人的回廊步入内室,迤逦的裙裾曳过寂静,似月夜深处漂浮旖旎的暗香,晶帘绰绰洒下疏影,隔着里面子昊独坐在案前。她却并不急着入内,抬手拢了一串冰玉倚帘看他,他也暂未说话,待手底一字书尽,才问道:&ldo;走了吗?&rdo;
&ldo;嗯。&rdo;子娆随意应了一声,仍借着灯火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过了会儿,她轻唤他的名字:&ldo;子昊。&rdo;
子昊抬头看她一眼,以目相询。她眉间若有冷月般的清郁,语声却比平日更多柔婉:&ldo;区区一个卫垣,以你的手段,轻易便可要他甘心听命,却偏要弄得他惴惴不安,再让我去笼络安抚,未免多此一举。&rdo;
子昊笑一笑,淡淡道:&ldo;今日有些倦了,不想多言,你去倒比我要好些。&rdo;
子娆黛眉轻拢,散开珠帘移步案前,隔了莹莹微光寸寸探索他眼底幽深的痕迹:&ldo;你别哄我,你心下想些什么,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rdo;
子昊安然与她相视,又是静静一笑:&ldo;既知道,怎么还问?&rdo;
子娆欲驳他,却张口无言。水晶盏中灯花微微一跳,映得她腕上串珠幽亮闪烁,恍然记起,其实多年之前他便如此,由商容至苏陵,由十娘至聂七,由墨烆至离司,一点点殚精竭虑的经营,赌上性命的博弈,暗底里聚积起冥衣楼这样的力量。庙堂死,江湖生,濒临覆灭的王权移花接木,盘根错节渗入诸国,形成潜伏的暗流布控天下,才能有如今从容的局面。
背负着重逾生命的责任,行走于血刃尖锋上的他,费尽了周折,冒尽了风险,耗尽了心血的谋划,而今唯一能号令冥衣楼七宫二十八分座的信物,却是她自幼贴身佩戴的小小串珠。
冥衣楼,那是他送她的及笄之礼。
那一日擦身而过,他淡定低语轻轻飘过耳畔,是她心中永世不灭的火焰,玄塔底下曾支撑着日日夜夜孤独与黑暗的侵蚀。
子娆,哪怕天地尽毁,我也会护你一生平安。
是不必再问,他对卫垣冷颜相向,做了她控制这权臣坚固的基石,任她踏着一步步迈向云间巍峨的天阙。九重云端极高极冷,与那玄塔深处一般无二,琼台峻宇都笼在煌煌天光之中,却是一片死寂的荒芜。
子娆做过这样的梦,于一天华美的虚空中寻找他的身影,看得到他的微笑,却触不到他的暖。此刻月色落于他的襟前,清幻如陷梦境,子娆心头惊悸,指尖蓦地扣住案头,几将那丰艳丹蔻也折断。忽然间,她额角微微一痛,被他抬手轻弹了一下:&ldo;傻丫头,莫要胡思乱想,你离让我安心放手还差得太远呢。&rdo;
他的笑容清淡,略带难得一见戏谑的痕迹。子娆先是有些怔忡,突然间凤眸照他一挑,狠狠盯了他漆黑的眸心,语声因低抑而略有微颤:&ldo;我最讨厌你这样,什么都算计在自己心里,什么都藏在自己心里。&rdo;
她以眉间冷丽的嗔怒,拒绝他波澜不惊的微笑。他不急亦不恼,一时低头轻轻地咳嗽,末了便顺着她道:&ldo;有什么事你想问,我答就是。&rdo;
子娆以眼角余光瞥他,却再怎么赌气,也在他润了笑意的注视下无法坚持,终要向那双透人心肠的眼睛屈服下来。没什么想问的,纵然不说不言,他的一切从未瞒她。
因为知道得太清楚,所以再没有丝毫任性的余地,他肩上的责任又何尝不是她同样无法逃避的命运?垂首敛眉,终叠起幽净的目光,轻轻开口:&ldo;既已选定了楚国,为何又要在穆国那儿费这么深的心思?&rdo;
子昊垂眸静默,片刻之后,复又微笑看她:&ldo;这几日有意无意,常听你提起夜玄殇。&rdo;
子娆道:&ldo;魍魉谷中他帮过我,之后因皇非针对于他,我曾用你的私印传书卫垣要他暂且退兵,为此还被你罚背了五篇《国策》,这些你都知道的嘛。&rdo;
子昊一笑,问道:&ldo;他较之皇非如何?&rdo;
子娆奇怪地道:&ldo;少原君权倾楚国,实力雄厚,一举一动皆可左右天下大势。穆三公子现在仍是他国质子,因遭太子御猜忌,身边杀机四伏,处境险恶,按今晚卫垣透露的消息,他如今在楚国怕是要有更大的麻烦,你难道不清楚?&rdo;
子昊微微合目摇头:&ldo;我是说夜玄殇较之皇非。&rdo;
子娆侧首思量,心中将这两个男子回忆比较,却也分不出个高下,只当他要了解两人以作决断,便细细说与他听:&ldo;皇非看去风雅倜傥,却有时傲气凌人,夜玄殇生性狂放不羁,实际心细如发;若论武功,逐日、归离两剑不相上下,想必难分胜负;若论谋略,一个谈笑用兵天纵奇才,一个手段不凡气度过人,日后恐皆非池中之物,你说孰优孰劣?&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