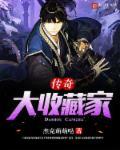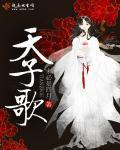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近代中国史纲在线阅读 > 第113章(第1页)
第113章(第1页)
----------
1康有为中举迟三年
七月,康在北京创刊《中外公报》。八月组织&ot;强学会&ot;,参加的有京官陈炽、沈曾植及道员袁世凯等,梁启超为主要负责人,曾获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等的赞许。守旧大臣徐桐、刚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则加以攻诋。康旋往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发行《强学报》,入会者有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等。黄遵宪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一八九〇年出版的《日本国志》是他的名著,其中关于明治维新的记述,对于读者颇有影响,康为其一。张謇受知于翁同龢,汪康年与张之洞接近。一八九六年一月,北京强学会与《中外公报》遭受封禁,上海强学分会与《强学报》亦停。黄遵宪、汪康年改办《时务报》(旬刊),梁启超主笔政,撰《变法通议》诸文,谓各种制度无时无事不变,今日尤需要变,主动求变,否则必为列强分割而亡国。以往的自强新政无不仰助西人,只利于外国,中国反蒙其害。&ot;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ot;变官制应伸民权,中国二千年来,君权日尊,国威日损,如设立议院,使君权与民权合,议法与行法分,自然可强。再不变法,可能发生革命。最好是采英国、日本的办法,行民权而不取民主。梁得文字奇诡,一时争诵,数月之内,《时务报》销行一万余份。一八九七年,又编印《西政丛书》,计三十二种。设大同译书局、女子学堂、不缠足会。时康创刊《知新报》于澳门,开&ot;圣学会&ot;、&ot;广仁学堂&ot;,发行《广仁报》于桂林。风气素称闭塞的湖南,由于巡抚陈宝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与地方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辈的领导,创设&ot;时务学堂&ot;、&ot;南学会&ot;、《湘学新报》(旬刊)、《湘报》(日刊),举办各项新政,气象顿变。梁启超应聘主讲时务学堂,中学以经史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而以兴民权为救国途径。南学会为一政治团体,集合南省志士,讲求救亡之策,有总会、有分会。地方有事,公议而行,具有议会规模;万一华北不保,南省仍可自立,为国家留一生机。梁任教虽仅四月,而留下的影响则继长增高。
----------
1公车指举人言
谭嗣同(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倾心于王夫之、黄宗羲之学及龚自珍、魏源的议论。对康有为十分景仰。著有《仁学》,强调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性,必须冲决一切束缚网罗。今日外患已深,&ot;分割兆矣,已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ot;。痛斥满清当道之愚与私,甚至说中国&ot;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ot;。君主为公众所推举,君权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会近于康的大同,而措词则多为激别。
倡导维新的人物,无一不受到西方的影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的为严复(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严为闽人,十四岁至二十七岁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及英国海军学院受过八年的科学教育,有过五年军舰实习经验。二十八岁起,总理天津水师学堂教务十五年。甲午战后,他认为西方之胜于中国者,不仅在器械而在政教风俗,其所以富强,由于公理日伸。中国不惟不足以当西洋,&ot;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ot;,因决以言论警世。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连续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精辟之论,与《时务报》南北相应。他说西洋命脉之所在为&ot;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ot;。中西事理之最不同处,&ot;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ot;。中人主恒,西人主变。所以西人日进无疆。讲富强、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术。富强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ot;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ot;,&ot;民之自由,天之所畀&ot;。今日之要政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施的事项莫亟于废八股,即汉学、宋学、词章亦皆宜束之高阁。他复就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理,阐发救亡的论证。一八九六年刊行所译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tionandethics),就自强保种事,反覆致意,使读者怵焉知变。1
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维新人士最活跃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为湖北、江西、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等省。他们的机构有学会、报馆、学堂。参加公车上书的举人散归各地后,自有推动的作用。学会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据说多至百余,报纸亦由十九种增至七十种。清代禁止士民结社论政,现在已被打破。
第二节短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
一、变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来中国的新政,始终以海防为中心。经过长期经营,多以为纵不能抗衡西方大国,要足以与日本相敌,而事实证明大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认为应改进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谓兵为立国之本的李鸿章亦称道日本各项政治日新月异,中国亦宜于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国人才无教,学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并不能转移大局。在他当权之日,尚不克大有作为,此时更不待言。翁同龢为光绪的近臣,对于新学西政,所知无多,但不失为有心之士,尽力启导光绪的政治观念,光绪十九岁时(一八八九),翁为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他留心洋务。一八九一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汤震的《危言》、陈炽的《庸书》进呈,并读《泰西新史揽要》,翁盛称他英爽精明。翁接触过不少维新人物,1颇赏识他们的才学,承认变法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