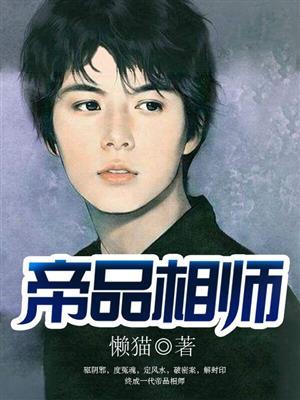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星光伴我行作文600字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无端端的,我想起了珍妮,阿甘的美丽的女友,在最幸福的时候,恶性的病毒让她永远离别了自己的爱人。杜冷丁,杜冷丁,那是种什么样的东西!诗琳,诗琳,你现在是在走着她那样的毁灭之路吗?
诗琳,我倒宁愿你此刻与新的恋人在享受南海的晴空与丽日,在欢笑和幸福中尽情翔扬,我愿你过得幸福,至少要比我幸福,而万万不想、不愿见到,你这般的模样。所有的梦幻已经破灭。我感觉自己像是死了,那么沉,那么冷。
我冷得发抖,对着海水和雨天长叫,愤懑无比。我跌跌撞撞地走回了住处,坐在墙角,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一句话也不说,一顿饭也不吃。一天一夜里,喝了两枝啤酒,没有喝醉,只是在浑身的痛楚中,任思绪泛滥。
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诗琳。这样的答案。好苦好痛的答案。半年来的所有揣测,所有思念,所有的心底的伤与痛,最终的交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样。我还是做那个最傻最傻的男人吧,向你大声地问一句:为什么!
坐在一株开得正热烈的木棉树下,火红的木棉花如雨点般不断自我身旁落下。我的手里,拿着一枝尖利的木棉树枝,心里面有着无尽的苦痛。那时,我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我把衣服掀开,用手去摸,好像没有感觉。再低头,这树枝上有三四朵木棉花,这样可爱,热烈,支撑着它们的枝干是那样的粗硬和丑陋。看着那枝节末端尖锐的劈开的茬口,对准了自己心脏所在的位置,把尖锐的枝端刺进自己的皮肤。血一点点地渗了出来。感到一阵的痛楚,也感到巨大的欣慰和愉快。那就像是一把生满了铁锈的锉刀,一点点地在胸膛上磨动,切割,拉断胸腹间的皮肤。然后自己用手扒开胸腔,右手插进去,拉断骨骼,揪紧自己的心肝,用强有力的手揉搓着,再用那锉刀一块一块地屠戮,在上面留下无穷的血洞,让每个血洞都向外汩汩地冒着血。找一扇厚重的石磨,把内脏一块块在就在身体里面连着神经给磨成齑粉。那时候,血液混合了肉渣与碎沫,自我的手上滴下,沾染湿透了脚下的布鞋。然后,我则拖着一行行的血迹,在木棉树下走来走去。手上加大了劲,血涌了出来,满手满身都是。心上的痛楚似乎是大大的减轻,换来是身体上的尖锐的疼痛。我感到自己想笑,并且没有掩饰这种伟大的情感,真真的笑了起来,狂笑着,就如同一个疯子。用鲜血浸染的花分外艳丽。这样会使我痛苦的心稍有些安慰。那时候,这狠心的女孩应该还会为自己滴一两滴眼泪吧。
&ldo;我就这样把自己的伟大的生命了结在这狠毒的女人手里,我要看看她的眼角是否会有因我而下的泪。我要叫她知道后悔……&rdo;
我发狂般地打电话给柯克让他赶紧回来。然后我去质问你的父母,去质问那个男人,去质问所有知道你近况的朋友们,但他们都保持着静默,这更让我怒狂不已。
这天,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你的电话。诗琳。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你说你已经在医院戒除杜冷丁成瘾了。是你的父亲强行把你送去的,说戒不了毒他从此以后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你也接受了。你打电话给我,满是道歉和追悔,但说事已经至此,无可挽回。你要我别去看你,因为你希望着在我心目中仍能保持以前的快乐形象,但是这样的形象,还会存在着么?然后,你突然挂了电话,我听到,在挂下电话前的一瞬,你哭了,很伤心很伤心的哭。
我跳上出租车,让司机去医院。但是,但是,你不见我,无论如何也不见我,你让医生把你锁在房间里,与我隔门相对,这实在让我难以理解!
你哭着说阿城对不起,我不是个好女孩。你也是看海岩的小说看得多了,总相信自己的身边,有着故事里一样的永恒的爱情和不变的真心。而其实在实际中,爱情就如同一根头发丝一般脆弱,长时的分隔,更合眼缘的对象的出现,生活的变故,等等,都会让本已经弱不禁风的爱情之桥立马崩塌。你说最起码的一点,你根本无法接受一个近乎半年时间都不在自己身边的男友,而这样男友的未来,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严酷。
诗琳,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早已相信。即使是现在的我,在部队院校已经生活了近半年,却还仍看不清自己未来的路,更别提你这样对部队一无所知的姑娘了。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你不会有一丝的埋怨,我只希望你的健康尽早恢复。
我在医院的走廊外徘徊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听着里面似乎传阵阵痛苦的呼喊,不知道是别人的,还是你的,我心里戚然。到了晚饭的时间,柯克到了,也与我一同,坐在墙角。我们没说得上一句多久不见的话,只是沧然地互相看着。
以后的几天,都是如此。我与柯克都非常抑郁,一个春节也不见多少欢笑。惟一稍感欣慰的是,你父母进去后,总会出来告诉我们,你的情况较之前一日又好了多少多少。一个人没有希望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给了他希望,让他为之付出一身的力气,却把这个希望狠狠地打碎。
我的假期马上要结束了,诗琳。看着你的现男友天天在医院外守候,痴痴地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你,请原谅我不能总守在外面了。我不想也不能让你的生命也节外生枝。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