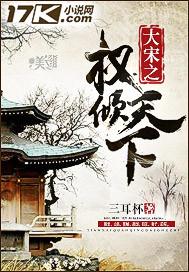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周国平 > 第132章(第1页)
第132章(第1页)
但这又怎么可能!并且如果她不知道任何关于你的新消息,为什么她不说些关于你的旧事呢?
如果她不想谈论你,当她谈论过去的事情时,为什么她不像从前那样,至少提起你的名字呢?但是,没有,这一切她都没有做;相反,她让我一直闲荡着,谈论一些难以置信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布雷斯劳、咳嗽、音乐、丝巾、胸针、发型、意大利的假期、滑雪橇、用珠子装饰的包、式样呆板的衬衫、袖口链环、维克托&iddot;雨果、法语、公共浴室、沐浴、烹饪、哈登的事情、经济形式、夜间旅行、皇家旅馆、帽子、布雷斯劳大学、亲戚们‐‐简而言之,谈论了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不幸的是,唯一与你有一点点联系的话题也是由几个关于金字塔、阿司匹林这样的词组成的。
这什么我花这么长的时间谈论这样的话题,为什么我会喜欢让那两个词从我的口中说出来,这真是让人惊讶的事情。但是,真的,将这些作为今天下午唯一的结果,我并不满意,因为几个小时以来,我的头脑满是想要听到&ldo;菲丽丝&rdo;这个词的念头。最后,我有意将我们的谈话引到关于柏林和布雷斯劳之间的铁路上来,同时,给了她一个险恶的表情‐‐面无表情。
无奈人生
第105章韩石山:你就是我的从前
远远地就看见了他。近了,更近了,在他扭过脸来的时候,不经意地,也是轻微地,我点了点头。他没有觉察,好,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在我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机关门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灰黄色的夹克衫,袒露着半个胸膛,黑蓝色的裤子,裤管挽得老高,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鞋带是一截细细的电线。夕阳的余晖,透过街树的罅隙,照在满是沧桑的脸上,他正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人行道上过往的红男绿女;眼里一丝忧愁,一丝迷茫,更多的是赏心悦目的喜悦。
在他的身旁,是一辆收废品的小平车,铁皮做的,漆成墨绿色的那种。这是这个城市多年前的一项德政。进城收废品的人,必须买一辆这样的平车。是一种标志,也是一种认可。车上是踩扁了的废纸箱,堆得高高的,如同满满一车金黄的谷禾。一天的奔波劳累,也是一天的收获之后,他在享受着这傍晚的小憩。那边过来一个美妇人,他几乎是贪婪地盯住瞅,二郎腿晃悠着,脚尖儿还一起一伏地打着拍子。我不由地笑了。他正瞅着那边,不会看见我。
离得更近了,就要到跟前了,仍是不经意地一瞥,我心里想着:朋友,你好,你就是我的从前,可你比我那时候好多了。
四十多年前,高考过后,回到了老家的村子。考试的成绩,自我感觉尚可,可我知道,能不能录取跟分数没有多大关系,全在政策的宽与严,宽一点说不定会乘隙而入,严一点就只能回村务农了。那是1965年,经过&ldo;四清&rdo;之后,农村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像我这样的本地高中生,最好的出路是当个民办教员,到一个小村里教书,若是村长支书看不上眼,那就只有劳动一途了。而一个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年,只能是做最重最脏的活儿,年纪再大些,就是挨家挨户掏茅粪了。这是我最为害怕的。想一想都让人了无生趣。
万幸,一个月后,通知书下来了,虽说不是自己理想的学校,好赖总是个大学。长长地嘘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逃出了农村。
五年后,大学毕业了,来到吕梁山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说是中学,实际上只是小学加一个班,叫六年级。小学是五年制,这个六年级就是初中班了。住处是庙里的一间窑洞式的偏殿。一到星期天,本地教员都回家了,庙院里就我一个活人。
又是一个星期天。夜深了,正在灯下看闲书,忽然院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谁呢,抄起火柱拉开门闩走出去,只见月光下一个人影正悄悄地朝对面的杂物间跑去。
&ldo;干什么的!&rdo;壮着胆子喝问一声。
&ldo;韩老师?&rdo;一面轻轻地回应着一面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
到了跟前,借着白麻纸窗户映出的灯光,看清了,是村外砖窑上扣坯的那个河南小伙子,人们都叫他大李。每天晚饭后,我总要去村外转悠,去了总会路过砖窑,次数多了,就认识了大李。
&ldo;去那儿做什么?&rdo;我指指杂物间,疑心他是想偷什么。
&ldo;韩老师,进去再说吧。&rdo;
进到窑房里,灯下才看到他一脸的惊恐。
&ldo;出了什么事?&rdo;
&ldo;抓流窜。&rdo;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说抓流窜,不是说他要抓别人,而是别人要抓他。在晋西山区,把那些外来打工的,一概叫做流窜,主要是河南山东一带的人,大多是做打土窑、扣砖坯一类的苦重营生。抓的时候,往往是趁晚上,民兵们带着枪,摸到砖窑上,抓住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送到公社集中。然后再押到县上,送到国营的砖场或是煤矿,挣够了路费再派人押送回原籍。
&ldo;来了!&rdo;我还没回过神来,大李便噗地一下吹灭了灯。
院里响起沓沓的脚步声。转了一圈,走了。
重新点起灯,我跟大李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河南内黄人,在老家上到高中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业停了,老家生活不好,就跑到山西来下苦力挣钱。我所以几十年后还能记得这个县名,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刘梅,一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老大学生,就是河南内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