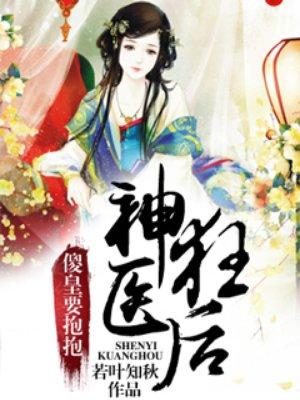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静静的顿河是什么主义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一个于旱的夏天。村边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腾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到对岸去,连脊背都湿不了。夜里,沉闷的暑热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于蓬蒿在燃烧,甜黎像一层看不见的薄幕挂在顿河岸上。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是连一个雨点也没有落到炎热煎烤的大地上,电光在空中闪个不停,夜空被划成一些带尖角的蓝色块块。
猫头鹰夜夜在教堂的钟楼上号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子上空回荡;这时猫头鹰却从钟楼上飞到被牛犊践踏过的公墓里,落在荒草丛生的褐色坟头上,悲鸣不已。
&ldo;灾祸临头啦,&rdo;老人们一听见猫头鹰在坟场上的叫声,就预言说。
&ldo;要打仗啦。&rdo;
&ldo;在俄土战争那年,也这样叫过。&rdo;
&ldo;也许又要闹霍乱了吧?&rdo;
&ldo;夜猫子从教堂飞到埋死人的地方去,就别指望会有什么好事情啦。&rdo;
&ldo;哦,大慈大悲的圣徒米科拉……&rdo;
沙米利&iddot;马丁,独臂的阿列克谢的弟弟,在坟场的围墙下,一连两夜守候着这只恶鸟,但是看不见的神秘的猫头鹰无声地从他的头上飞过,落在公墓的另外一头的十字架上,把令人心惊的叫声散布在朦朦胧胧的村庄上空。马丁下流地骂了一阵,向飘动的乌云放了一枪,走了。他就住在这附近。他的妻子是个胆小多病,像母兔一样多产的女人,‐‐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她一看见丈夫就责骂起来:&ldo;混蛋!你这个道道地地的混蛋,该死的东西,它碍你什么事儿,啊?要是上帝怪罪可怎么办?我马上就生孩子啦,要是为了你这鬼东西的罪过难产可怎么办?&rdo;
&ldo;住口,你放心!你是不会难产的2你已经生惯啦,胎胎都像箍桶匠的马生得一样痛快。难道就让这讨厌的玩意儿在这里吵人心烦吗?这个魔鬼,它会把灾祸叫来的。要是打起仗来‐‐就要征召我人伍,看你养了这么一大堆,&rdo;马丁指着墙角说道,那里,在车毯上胡乱躺着几个孩子,有的在尖声哭叫,有的正在打呼噜。
麦列霍夫&iddot;潘苔莱在村民大会会场上跟老头子们谈话的时候,很郑重地说道:&ldo;我家的葛利高里来信说,奥地利的皇帝到边境上去过,还下命令把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一处,准备向莫斯科和彼得堡进军。&rdo;
老头子们追忆着过去的几次战争,交换着彼此的想法:&ldo;从年景上看,好像不会打仗。&rdo;
&ldo;年景和打仗毫不相于。&rdo;
&ldo;大概是学生们在捣乱。&rdo;
&ldo;这种事情咱们总是知道得最晚。&rdo;
&ldo;就像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样。&rdo;
&ldo;给儿子买了马没有?&rdo;
&ldo;用不着预先……&rdo;
&ldo;这是瞎说!&rdo;
&ldo;可是跟谁打仗啊?&rdo;
&ldo;跟土耳其打仗是为了争大海。可大海是分不开的呀。&rdo;
&ldo;那有什么难分的?就像咱们分草一样,把大海分成一块一块的,你就分吧!&rdo;
谈话开始变成开玩笑,老头子们也就渐渐散去了。
短暂的割草时节正等待着人们,顿河对岸的各种草都已经开完了花,那都是些没有一点香气儿的病弱的草,不像是草原上的草。同是一样的土地,可是草吸收的养分各不相同;山岗后的草原是上等黑土地,像脆骨一样:牲口群跑过去‐‐连个马蹄印都看不见;坚硬的土地,长出来的草也肥壮、芳香,齐马肚子那么高;但是在顿河边上和顿河对岸,却是一片潮湿的松软的土地,长的全是些不很茂盛。没有用处的矮草,有的年头,连牲日都讨厌吃这些草。
全村一片磨镰刀的声音,耙子也都刨光了,妇女忙着给割草的人送克瓦斯,但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惊动全村的事情:镇警察局长和检察官一同来了,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满嘴黑牙、穿着制服的瘦弱的军官;他们找到了村长,会同几个见证人,径直就到斜眼卢克什卡家里去了。
检察官手里拿着一顶有帽徽的帆布制帽。大家都顺着街道左边的篱笆走去,太阳斑斑点点地照在小路上,侦察员一面用他那沾满尘土的皮鞋踩着篱笆的影子,一面对那个像公鸡似的往前跑着的村长说:&ldo;那个外来户施托克曼在家吗?&rdo;
&ldo;在家,阁下。&rdo;
&ldo;他做什么事情!&rdo;
&ldo;这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手艺人……整天都在挫啊、刨啊。&rdo;
&ldo;你没有注意他有什么活动吗?&rdo;
&ldo;一点也没有。&rdo;&lso;警察局长一面走着,一面用手指头去挤眉毛中间的粉刺;他累得直喘气,呢于制服热得他满身是汗。矮小的黑牙齿军官用一根草茎剔着牙齿,眼边柔软的红褶子皱了起来。
&ldo;哪些人常上他家去?&rdo;检察官拦住向前跑的村长,问道。
&ldo;是,常有人去。他们有时候玩牌。&rdo;
&ldo;是些什么人?&rdo;
&ldo;多半是磨坊里的工人。&rdo;
&ldo;究竟是些什么人?&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