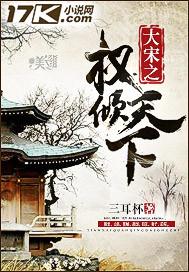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东宫女官免费阅读 > 第29章(第2页)
第29章(第2页)
其实在收到章岘那张写有“高处胜寒”的字条时,便已预想过甚至谋划过无数次重遇太子的情形,也预先想好无数种应对的方式,却唯独没有眼前这样的。
案前负手而立的玄衣男子转过身,阳光仿佛在那一刹那就散了,明光灿影,映出那俊美出挑的侧脸,幽邃黑眸,单薄双唇,唇畔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贵胄天成。
连槿有一瞬的松怔,待反应过来时,亟亟地垂下头,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波澜不惊:“皇后娘娘召见奴婢,奴婢奉旨前来,无意冲撞殿下,望殿下恕罪。”
祁珣抬眸掠了眼跟前神情还算镇静的连槿,唇角微微勾起,“母后在内堂虔心礼佛,可挪不出精力来见你这等无名婢子。”
连槿心里“咯噔”一声,难道让尹红蕖来寻自己的,不是皇后,而是眼前的太子?
若真是太子要见她,何必避出东宫,舍近求远地绕到未央殿?
避?难不成太子是用皇后为幌子,以此来避开某些人的耳目?
一个模糊的猜测在连槿的脑海渐渐显出雏形,虽不是十拿九稳,但眼下与太子独处的绝佳机会若是错过,她日后便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连槿上前半步,躬身轻轻吐字:“奴婢谨聆殿下吩咐。”
祁珣打量着她进退得宜的举止,唇角的笑意渐深,“果然是松石先生教出的徒弟,没有让孤失望。”
“松石”是章岘在前朝时的雅号,曾与“墨梅学士”方敬亭合称“文坛双璧”。但自从二十余年前因触怒天子,被赐宫刑后,他的举世盛名便随着避居掖庭,而被人们渐渐遗忘,杳然不闻了。
听得这个称谓从祁珣口中道出,连槿的脑子嗡然一声。
他作为当朝太子,对戴罪之身的章岘这般敬称,难道不是有失妥当吗?
他到底是无意之失,还是试探之举?
连槿依旧躬身恭敬回道:“恩师师承檀山仙人,自是博学多能。但奴婢愚钝,所学不过皮毛,殿下谬赞了。”
檀山仙人指的是贺兰家前任家主贺兰徵,他为助先帝登上九五之位出力甚多,而被先帝御封为国师,享尽尊荣。
用贺兰徵的御赐名号为章岘的罪臣身份做遮掩,是连槿此时所能想到的最佳之方,但却不知是否合太子的心意?
殿内的刻漏声,滴答滴答,一声一声似乎都砸在连槿的心上,惴惴不安,却不能表露出分毫,只能屏息等待着太子的回应。
祁珣看着连槿低垂着双眸的脸庞,不施粉黛的苍白,却没有丝毫怯懦,隐隐倒有几分迎霜傲雪的风骨。
他陡然想起她那锋刃毕现的字体,隽秀中透着的铮铮铁骨,的确不像是那种文弱懦小的女子。
“的确是玲珑心思。”祁珣嘴角含笑地悄然上前几步,她似乎没有料到他会靠得这么近,身形微微地颤了颤,却并未退后,依旧躬身垂首地笔直站着,面容淡然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