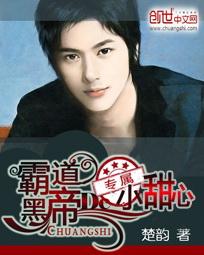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主要内容和读后感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佛教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在印度东部兴起的宗教之一,是反对西北部的婆罗门教的,所以佛祖坚决拒绝使用婆罗门教的经堂语梵文。梵文在当时还没有取得像后世那样煊赫的地位。它只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的语言,还没能成为官方使用的政治语言。
释迦牟尼悟到了教义,找到了一些徒众,有了一种供他使用的语言,于是就开始&ot;转法轮&ot;--传教。第一次说法的内容大概是关于&ot;四圣谛&ot;--苦、集、灭、道的,|福哇小!說下≈載站|此时当然还不会有什么佛典(kanon)。哥廷根座谈会上,学者们心目中的佛典是包括经、律、论一整套的典籍,这在释迦牟尼生时是根本不可能形成的。bechert说,最古的佛典是属于律部的,这是隔靴搔痒之谈,绝对靠不住。我想拿《论语》来作一个例子或者依据,推测一下佛教urkanon形成的过程。孔子的一些行动和同弟子们的一些谈话,被弟子们记了下来,积之既久,遂形成了《论语》。释迦牟尼恐怕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他常说的一些话,被弟子们记在心中,扩而大之,逐渐形成了一些经典中的核心。区别只在于,中国的《论语》保留了原型,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成套的有体系的经典,有如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新约》、《旧约》,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经典的形成走的是另一条路,结果形成了一套汗牛充栋的经典宝库,而没有一部为各派所共同承认的宝典。后世产生的经典也往往标出&ot;佛说&ot;,这当然是绝对不可靠的。
印度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文字呢?确切时间还不能十分肯定。反正阿育王(约公元前275年-232年)时代已经有了文字。有了文字,佛典就能够写定。写定的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二世纪末。在这里又出了一个佛典梵文化的问题,这个现象可能与佛典的写定同时并举。什么叫&ot;梵文化&ot;?原来佛典的语言是俗语,主要是古代半摩揭陀语。后来,这种俗语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不能适应需要。政治界和宗教界都想找一个能在全国都通用的语言,选来选去,只有原来被佛祖所拒绝的梵语最符合条件。于是就来了一个所谓&ot;梵语复兴&ot;(sanskrit
renaissance)。佛典也借这个机会向梵文转化,这就是&ot;梵文化&ot;。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初俗语成分较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俗语成分渐减,而梵文成分渐增。这样的语言就被称为&ot;佛教梵语&ot;或&ot;混合梵语&ot;(hybrid
sanskrit)。
以上是我在《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一篇论文中,对一九七六年在哥廷根举行的&ot;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ot;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论文的意见。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中,我又综合地讨论了下面六个问题:
第73节:回到祖国(26)
(一)什么叫&ot;原始佛典&ot;;(二)耆那教经典给我们的启示;(三)摩揭陀语残余的问题;(四)所谓&ot;新方法&ot;;(五)关于不能用&ot;翻译&ot;这个词的问题;(六)汉译律中一些有关语言的资料。
这些问题前面都有所涉及,我不再一一加以解释了。
4?《〈罗摩衍那〉在中国》(附英译文)
中国翻译印度古代典籍,虽然其量大得惊人,但几乎都是佛经。大史诗《罗摩衍那》虽然在印度影响广被,但因为不是佛经,所以在我的全译本出现以前的二千余年中中国并没有译本,至少对汉文可以这样说。我这一篇论文就是介绍《罗摩衍那》在中国许多民族中流传的情况的,共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罗摩衍那》留在古代汉译佛经中的痕迹;二,傣族;三,西藏;四,蒙古;五,新疆:(一)古和阗语,(二)吐火罗文a焉耆语;结束语。
前五部分的内容,我在这里不谈了,请读者参看原文。我只把&ot;结束语&ot;的内容稍加介绍。我谈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罗摩故事宣传什么思想?印度的两个大教派都想利用罗摩的故事为自己张目。印度教的《罗摩衍那》宣传的主要是道德伦常和一夫一妻制。佛教的《十车王本生》则把宣传重点放在忠孝上。至于《罗摩衍那》与佛教的关系,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弄不清楚。两者同产生于东印度,为什么竟互不相知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罗摩的故事晚于《梵书》,而早于释迦牟尼。
二、罗摩的故事传入中国以后,有关的民族都想利用它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傣族利用它美化封建领主制,美化佛教。藏族利用对罗摩盛世的宣传,来美化当地的统治者。
三、汉族翻译的罗摩的故事,则强调伦理道德方面,特别是忠和孝。我总怀疑这是译经的和尚强加上去的。中国古人说:&ot;不孝有三,无后为大。&ot;人一当了和尚,不许结婚,哪里来的&ot;后&ot;呢?而许多中国皇帝偏偏好以孝治天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中国佛教僧徒就特别强调孝,以博得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欢心,以利于佛教的传播。
四、中国人不大喜欢悲剧。罗摩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中国编译者则给了它一个带喜剧色彩的收尾。
五、罗摩的故事传到了中国,被一些民族涂上了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
最后,我谈到了《清平山堂话本》卷三中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这个话本一方面与罗摩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与《西游记》的神猴孙悟空有某些瓜葛。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顺便说一句:这篇论文有英译本。
5?《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第三十九张译释》
这里译释的是新博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第三十九张两页。详细说明已见一九八三年4,这里不再重复。
此文有英译文。见下面7。
6?《〈薄伽梵歌〉汉译本序》
我在这篇序言中主要介绍了印度三位学者对《薄伽梵歌》的意见,他们是高善必(d?d?kosabi)、basha和恰托巴底亚耶(插tadhyaya)。我认为,这三位学者对此书的意见各有独到之处,其余印度和印度以外的学者们的意见,多得不可胜数,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我一概省略了。在序言的最后两段中,我提出了一个&ot;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ot;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我脑海里不断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宗教发展的规律:用越来越少的身心两个方面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大越多的宗教的满足。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我曾专门讲过一次。我个人认为,这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观点或者规律。
7?translationfrotheto插rianaitreyasaiti-nāt&iddot;akathe39thleaf(2
pas)76yq1?3911and1?3912ofthexjiangeuversion
已见上面5。
8?《自序--〈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在这一篇&ot;自序&ot;中,我主要讲了我学习&ot;佛教梵语&ot;开始时的情况,接着又讲了我写《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的来龙去脉。《再论》写于一九五八年。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德国梵文学者、我的朋友bechert的。在这一篇&ot;自序&ot;的最后,我提出了我研究&ot;佛教梵语&ot;的用意。我不是为研究语法变化而研究语法变化的,我希望把对佛教梵语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