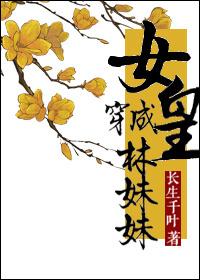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日照金山文案短句干净治愈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眼前忽然拓下一片阴影,周旋回过神,思绪从久远模糊的回忆中挣脱出来。
她拾掇好情绪,表情如常,好似刚才唐遇礼看到的都是错觉,“都收拾好了?”
唐遇礼点头,目光扫过周旋掌心浅淡到几乎看不分明的痕迹,他温声道:“差不多了,先回去吧。”
说完,周旋看到他从禾苗的书包里拿出一捆卷成筒的画纸递了过来,“这是苗苗的画,你不是想看吗?”
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周旋从中看到一丝夹杂在探寻中略带安抚的意味,好像看出了她情绪不对劲,随意找了个由头转移她的注意力。
周旋将固定的皮筋摘下戴在手中,展开画纸低头看了起来,她看得专注认真,目光轻柔地铺落在纸张之上,眼里有种对待所钟爱事业的沉迷,从始至终也不曾抬头。
耳边如风寂静,周旋一直低着头,注意力集中在眼前,不曾察觉身侧男人时不时投来的冷沉视线。
直到平直的羊肠小道走到尽头,即将跨入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周旋感觉手臂被人扯了下,低沉磁性的男音浮在耳际,“看路。”
周旋抬眼,见他一只手牵着禾苗,另一只正握着自己的胳膊,两相对比,情景莫名令人发笑,“我又不是苗苗,你不用看小孩一样看着我。”
见她步入正轨,唐遇礼收回手,“苗苗比你省心。”
听到他这幅以长辈角度出发的口吻,周旋更想笑了,从来没人拿她和小孩做比较,更何况在这种不知出于什么标准的对比之中她还落了下乘。
“禾苗哥哥,你是不是搞错了?”
唐遇礼余光扫来,没出声应和也没有置之不理,给了个眼神示意,静待她的下文。
周旋继续说:“你刚才说话的口气很像一个家长在抱怨自己的小孩不听话,搞搞清楚,你是禾苗的哥哥,不是我的哥哥。”
唐遇礼漆黑的双眸盯着她,步子不停,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平静回击道:“左一句哥哥,右一句哥哥,周旋,你想暗示我什么?”
如果不是他的表情和眼神都太冷静,看不起任何波动起伏,周旋一瞬间有种在听暧昧情话的错觉。
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不知收敛的调笑,进一步摸索唐遇礼的底线,试图寻找到他情绪变化的阈值,“你觉得我在暗示什么?”
几乎在她话音落下的同一时刻,那道清冷矜贵的目光不含情绪地扫了过来。
“当着小孩的面,你非要我把话说穿?”
明明是一句提醒她自尊自重的好意警告,言辞表露中也是给足了她最后的体面,劝告她适可而止,不要越线。
然而从那张孤高傲然的口中以淡薄语气说出来,周旋不仅没有被那股明显外露的疏远气质所震慑,甚至罕见地感受到胸口近乎逆反而涌起的汹涌澎湃的兴味。
已经到了即将捅破窗户纸的地步,即使他对自己的企图一眼见底,也并没有装傻充愣企图糊弄过去,而是坦然将那层看似平静的纱布撕开一层,却几次三番在她想彻底撕破脸皮将叵测居心摆到台面时,硬生生叫停她的行为,以此竭力护住两人之间只要谁都不越界,依旧能勉强维持和睦关系的防线。
尽管,这层关系在她不知好歹的挑拨下,已然变得岌岌可危。
但周旋仍然很想知道,如果她真的撕破那层形同虚设的窗户纸,唐遇礼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自欺欺人。
这是一场基于游戏胜负欲的实验,而唐遇礼,就是她绞尽脑汁进行研究,想要窥破他不止于展露人前清高疏离、冷情到仿佛什么都动摇不了他的面孔之下,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是否恰如其分地互为磊落证明,抑或只是伪装得当的灯下黑。
搞艺术的通病,就是容易发疯引证某种满足自身恶趣味的猎奇理论。
即使是两种无论从材料还是色泽都再相仿的色系,在同一张纸上按照不同比列进行融合兑染,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新色块。
纸上学来终觉浅,也永远停留在枯燥的理论阶段,而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行色彩渲染,可比画画有意思多了。
她已经找到最完美的画纸,现在,只需要把颜色一一堆叠上去,然后静置冷落,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观察到实验结果。
究竟是颜料作为无法抗拒的异物入侵画纸本身,达到玷污上色的效果。
还是画纸在颜料的淳淳引导下,由内向外渗透出更浓烈阴暗的色彩,表明画纸本身就不纯洁。
也许这个过程会无比漫长,但周旋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
按耐住强烈到几乎要从胸口溢出吞没自己的战栗,周旋感受到心跳猛然加快,快到理智的防线随时就要在拉扯中断裂,迸发出失控的情绪。
她扭头看向唐遇礼,挑衅的声线微颤,“你大可以试试,反正丢脸的不是我。”
“不过,”周旋微微一笑,明艳眉眼满是肆无忌惮的笃定,“你敢吗?小唐僧师傅。”
敢在禾苗面前,把善男信女那套不入流的风月手段说出来吗?
敢当着我的面,用厌恶嫌弃的口气指责我的行为是一种近乎骚扰的有伤风化吗?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嘴皮子上下一动,几句对谁都能说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口头蜜语。
无论是在无趣挣扎里厌烦,还是清高俯视中凝望。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