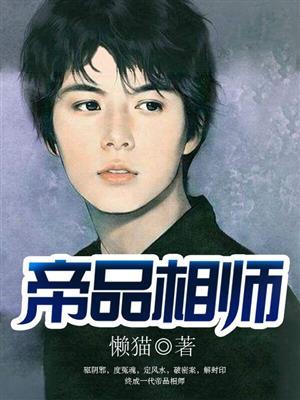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汉武挥鞭是成语吗 > 第六十四章 悲催中行説(第1页)
第六十四章 悲催中行説(第1页)
中行説满脸不悦,用看傻子的目光不断打量着状若癫狂的刘彻,久久不语。
半晌后,刘彻才恢复正常,带着笑意道:“如此看来,孤王实在不得不感谢你啊!你可记得,我朝高祖和冒顿单于定下的盟约,‘长城以北,引弓之国,承明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你以为如何?”
中行説不屑道:“此等城下盟约,对于我匈奴,自是好事;对于你汉国,堪称国耻。”
刘彻摇摇头,面露感叹之色:“我朝高祖仅用七年,从一介布衣,成为这大汉天子,各种心思算计,岂是你能猜度的?引弓之国,冠带之室,好深的布局,好大的陷阱,可怜你们匈奴中计而不自知,可悲可怜啊!”
眼见中行説张嘴欲要反驳,刘彻摆手制止,頽自继续说道:“秦末时,匈奴人曾宣称本身是夏朝后裔,时值中原战乱,诸侯均未对此有过异议,从而使他们具备了入主中原的名分。若匈奴当时在礼制上向中原模式做些改变,最大程度减弱身上蛮夷的成分,中原那一些有才能却未受重视的人必会前去效力,跟我大汉争势。夷夏之争,争的起根不是血统,而是道统!
想来当高祖朝派遣至匈奴的使者,发现匈奴人崇尚汉地的食物衣服,对于汉民的礼节也很风尚时,我大汉的君臣们定会遐想起前朝秦国由夷入华夏的发迹史,从而越发芒刺在背。白登山一战,高祖固然败了,却借机给匈奴下了一个套子,将‘引弓之国’的蛮夷帽子死死扣在匈奴的头上,永远失去了入主‘冠带之室’的名分!”
中行説闻言,面色铁青,嘴上却讥讽道:“这些不过是太子的妄自猜测,意图粉饰你先祖的失败罢了,如此自欺欺人,实在可笑得紧。”
刘彻不以为意,继续道:“那就不说高祖,且谈谈我祖父文帝吧。据传你叛逃匈奴后,文帝曾派遣使者到匈奴,嘲笑匈奴风俗没有礼义,言下之意,匈奴人是野蛮的。而你当面驳斥了他,与他辩论后大获全胜,使他的轻薄不仅没有当场激怒匈奴单于,反而致使单于全力支持你严禁匈奴人风尚汉民仪态礼节。你可还记得此事?”
中行説阴沉着点点头,这场汉匈礼义之辩奠定了他在匈奴的地位,他数十年来一直引以为傲,如今倒要看着牙尖嘴利的汉国太子会如何评价。
刘彻端起茶杯,在手中把玩了片刻,满脸戏谑道:“文帝遣使和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稳住匈奴,免其侵扰边境。是以和亲后,本应不会去做任何激怒匈奴的事。你叛逃时正是和亲后不久,文帝却很诡异地派去轻薄的使者,在匈奴取笑匈奴人的风俗。不但如此,使者还会被你这样一个从未治学的宦官辩驳得哑口无言,可见这个使者是不稳重并且也口齿不伶俐的人。
需知中原盛产辩士,我大汉立国后,就出现过刘敬和陆贾这样的顶尖辩士。很难想象,文帝往匈奴遣使时,会找不到一个辞锋锐利的人。即便找不到,找一个稳重的人应该不难吧?找一个轻浮之人去冒搬弄匈奴之险,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行説脸色大变,却无可辩驳,刘彻的推论并没错,当年的使者的表现确是讷于言却疏于行,如今想来,确有几分诡异之处。他后背的衣裳瞬间被冷汗浸透,似乎猜到了刘彻话中的意思。
刘彻见状,看出他已抓到了一丝头绪,随即继续打击道:“其实白登之围后,匈奴仍具备窥视中原的意愿和前提,只要变俗,就能告竣。而在文帝朝,匈奴已露出了变俗的苗头。如果匈奴变俗乐成,那汉匈两国的态势只会向对于我大汉愈来愈糟的方向演变。而文帝当时还不能凭大汉的力量去扑灭这一苗头,一是力量不足,大汉还没有从秦末称霸的战役创伤恢复过来;二是大汉内部出现的新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分封的诸王在渐渐坐大,在未能确定匈奴对于大汉无代替意愿之前,文帝还不能分出手脚解决诸侯王。
大汉在那个时候只能期待匈奴本身去扑灭变俗的苗头,成为一个对于大汉只有伤害能力而没有倾覆意愿的国度,从而为本身争取到时间,休养以及解决内部问题。正是因为你的叛逃,匈奴成为可一个固保守俗的国度,纯粹落空了时变的**。是你阻止了匈奴向中原地区演化的可能,使匈奴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机会革新制度的政权,从而使匈奴损失了争霸中原的前提,对于华夏只有掳掠的意愿而落空占领的雄图。这一现象,对于当时的大汉来说,是极为重要和极为及时的。
所以说,孤王今天得替先祖们好好感谢你!正是你,使得匈奴彻底成为排斥中原文明,对于汉境无占领**的国度!。。。。。。”
噗!中行説面色数变,喉头不断涌动,嘴中一甜,竟喷出一口暗红的血液,喷洒在观鱼亭光洁的汉白玉地面上,宛如一朵朵梅花,妖异而醒目。刘彻赶紧侧身避开,面上闪过转瞬即逝的快意,口中不断促狭道:“使臣何至于此,莫非承受不起孤王的谢意?倒是孤王孟浪了,怕是折了你的寿命。李福,赶紧让人将使臣送回去,好生照料才是!”
眼见李福招来几个内侍,将面如金纸的中行説抬走,刘彻随即摆出一副纨绔模样,晃晃悠悠的朝长乐宫行去,如今气煞了匈奴使臣,皇祖母那里还是需要提前知会一声,稍作安抚的。
是夜,未央宫御书房内。
景帝静静的听刘彻诉说完羞辱中行説的经过,不由开怀大笑起来:“常闻古人有言语杀人,不想你这臭小子也有这等本事。那中行説回‘蛮夷邸’后,仍气若游丝,虽说生机无碍,但免不得闭门休养一段时日了。”
刘彻点点头:“如此一来,他也就没精力去耍手段了。只是不知他此番原本作何打算,以后也好预先做些防备。”
景帝剑眉高扬,冰冷的目光仿佛凝聚成一柄柄利剑,遥指东南道:“还能有什么新鲜事?不管是谁,只要是不走正道的,明年出兵前都要全部处置干净!”
刘彻闻言大喜,知道皇帝老爹已经全盘接受了他昨夜的进言。
自从冒顿单于趁秦末大乱,南下夺取了河南之地(不是今天的河南省,是指河套地区),失去长城屏障的中原地区,就只能任匈奴铁骑驰骋纵横。只要大汉能夺回朔方,西河和云中三地,就可以重新掌控秦代长城,并以此为屏障,极大的降低匈奴铁骑的威力,拒敌于长城险关之外。如此一来,就可以给大汉足够的战略空间,彻底解决国内问题,并腾出兵力首先收拾掉西羌。
景帝随即又微微叹惜道:“只是皇儿今日对中行説所说的话,有些多了。”
刘彻一愣,仿佛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儿臣原本也只是妄自猜度,随意拿话挤兑他罢了,难道。。。。。。”
景帝无奈的点点头,苦笑道:“不错,皇儿误打误撞,还真是蒙对了。大汉开国之初,贤相萧何就定下了防匈奴入华夏的计策,只由帝皇口口相传,至今五十余年了。原本朕百年之前,也是要交代你的,谁知如今却无此必要了。不但你已察觉,还尽数让中行説知晓,朕实在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刘彻满脸黑线,果然必须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汉初的几位皇帝,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毕竟高祖刘邦血脉里的**气实在太过霸道,遗传了下来。之所以汉初的帝皇只有汉武帝比较热血冲动,只不过是他不如祖辈那么阴险狡诈罢了,所以他玩政治的手腕远远比不上祖辈和父辈,只能来硬的了。
刘彻暗自腹诽,却胸有成竹的安慰景帝道:“父皇无需多虑,明年出兵夺回河南地后,假以时日,匈奴不但无法再犯我中原,恐怕连大草原都呆不下了!”
景帝皱眉北望,幽幽道:“朕已着快马将你的计策给郅都送去,希望他能守住雁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