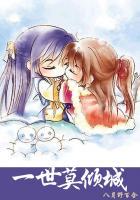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安德海简介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娘是在提醒儿子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可安德海偏偏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ldo;娘,做太监究竟有什么不好,你们都那么反对呢?&rdo;
&ldo;做了太监就不是正常的人了,他们不能娶媳妇,没有孩子,到老了无依无靠,很可怜。&rdo;
娘耐心地规劝儿子,说得安德海几乎打消了做太监的念头。
春去冬来,一晃四年过去了。安德海已变成了一位少年。
他已感到自己在向成年人迈进,这一年春天,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已开始发育,有一股青春的冲动,不过那一股冲动很快就消失了。这四年来,他虽然嘴上不再提做太监一事,而心里一刻也没忘记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爹娘不让他做太监,爹娘是希望自己为安家传宗接代,延续烟火。当然,这是一种责任,是一个作为男人的责任,安德海的心里也不是没想到过这些,可每当他累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时,面对一贫如洗、空荡荡的家,他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家庄二爷的家:高大的门楼上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摆着檀木家具,还有那顿顿红烧肉,件件绸缎衫,哪一样不让人羡慕。安德海也明白,到现在,安家连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也没有,不给汤家当长工,就得挨饿,就凭这双手,什么时候才能买田盖房?恐怕到了自己的孙子的孙子,也还不能盖上二爷家的那种瓦屋。像这样穷下去,传的宗,接的代也是穷一辈子,一代一代地穷下去,不如不去传宗接代。再说,即使是延续香火,也不是全落在自己的身上,不还有老二安德洋吗?
安德海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像爹那样,累一辈子,穷一辈子,而唯一通向发财的道路是做太监。这一回,他学聪明了,不再向别人透露心迹,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先自阉,生米煮成熟饭,再也无人阻拦。
这日,他把弟弟安德洋喊到跟前,认真地对弟弟说:
&ldo;咱家穷不?&rdo;
&ldo;穷&rdo;
&ldo;想过好日子吗?吃的好,住的好,穿的好。&rdo;
&ldo;当然想,可钱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rdo;
安德洋从小就依恋哥哥,信赖哥哥,是哥哥把自己带大,他已九岁了,对于同胞手足情,也多少体会了一些。
&ldo;哥,只要能让咱们过好日子,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rdo;
&ldo;哥现在什么也不让你做,不过,等将来你长大后,娶了媳妇,一定要多生几个儿子,为咱们安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rdo;
&ldo;那好办,那哥你呢?你娶了媳妇,不也能生儿子吗?&rdo;
安德洋当然不明白哥哥的用心良苦,前几年他还小,关于安德海想做太监一事,他压根儿也不知道,这些年爹娘怕提起此事,反而提醒了安德海,所以一直就没人再提到过此事。所以,刚才安德海的一席话,根本就没引起弟弟的多大注意。
&ldo;哥不娶媳妇,更不生儿子,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挣大钱。&rdo;
听哥说,他要出去挣大钱,安德洋很高兴。每当他跟爹赶集卖鸡蛋时,他都要在油条摊子前站上好一会儿,用力地猛吸带着
油条香气的空气,好让自己过过馋瘾。安德洋当然希望哥哥挣大钱。
&ldo;哥,你出去挣大钱,要不要跟爹娘说一声再走?&rdo;
安德洋认为哥哥明天就上路,天真地问哥哥。安德海似回答弟弟的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ldo;哪儿能走这么快呢,还有一些要做的事儿没做哩。&rdo;
这没做的事儿便是阉割。
四年前,听马家庄的二爷讲起过他十来岁时,被强迫阉割的经过,可那时自己还小,没仔细问清楚究竟该怎么割法,现在可把安德海给难住了。总不至于用刀剁去吧,不会那么简单的。
记得去年麦收的时候,眼见南边飘来一片黑云,为了赶到大雨前把地里的麦子抢回家,全家人赶割麦子,安德海一不小心,镰刀划破了手指,当时鲜血直流,疼得他直想掉泪,他咬紧牙关,用右手紧捏着左手,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止住血,但那伤口仍在疼,两天以后,还不敢碰那个伤了的手指。手指是无意中割破的,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可现在若要自己动手割小鸡,那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呀,能下得了那个狠心吗?
安德海犹豫了,别说是一个14岁的少年,哪怕是壮汉子,恐怕也硬不下这个心来,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硬硬地剜掉,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算了吧,这太监之门太难跨了,要跨进这门坎,首先要冒生命的危险,实在是太可怕了。&ldo;安德海呀,安德海,你也有一点痴心妄想了,发财挣大钱,一呼百应,权势无边,能是你这穷小子沾上边的吗?&rdo;
安德海在心里否定着自己,他决定打消自阉的念头,老老实实地种地,将来娶个媳妇,为安家传宗接代。
自从四年前,安德海与&ldo;汤包子&rdo;交上了&ldo;朋友&rdo;,安邦太一怒之下,误伤了&ldo;汤包子&rdo;,安家卖田赔礼之后,安德海与&ldo;汤包子&rdo;之间的仇恨就更深了虽说住在一个庄子里,但平时他们很少遇上,即使路遇仇人,他们也只是互相望一眼,并不搭话。
这日,安德海在山上打柴,他把一大捆柴扎好,用扁担挑着回家去,恰巧&ldo;汤包子&rdo;上去捉山鸡,两人狭路相逢,四目对视了良久,安德海咽了一口唾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