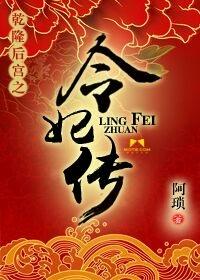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殿下让我还他清白全文免费阅读 > 第一百五十五章 正文完(第2页)
第一百五十五章 正文完(第2页)
阴沉沉的文德殿内,繁重华美的锦帘仍严严掩着四面高窗。
内侍噤声,大气不敢出地缩着脖子立在角落。殿中一片狼藉,地上尽是被摔得散乱的奏报上书,热茶翻在地上,漫开片片深浅水渍。
从御史台将那一封襄王供词呈递政事堂,参知政事亲自用印,明具诸状昭告天下,文德殿内日复一日,便都成了这般光景。
皇上坐在暗影里,这些天里,除了动辄暴怒绝望嘶吼,他就只这样一动不动颓然坐在龙椅之上。
倘若倒回当初,若有人胆敢递上这样一封罪君谤上的文书,甚至不必皇上亲自交代,就会有人来料理这些胆大包天的逆臣。
可到了今日,遍观朝野,他竟已连将这一封文书驳回的倚仗也没有了。
六年前,他机关算尽,借襄王之势尽除了心腹之患。
先帝重病,由他临朝监国,一步一步走至今日,原以为已将一切都握在手里,只等慢慢收拢。却不想无非是回来了一个人、醒来了一个人,便能将他苦心筹谋的朝局翻得干干净净。
萧朔与云琅出兵时,他还存着一丝念头,倘若北疆大败,朔方军全军覆灭,宫中尚能勉力一搏。可一日续一日地煎熬过去,等来的终归还是那封但凡有云麾将军出征,便定然能传回来的大胜捷报。
太师
皇上嗓子干涩的厉害,出声时一片嘶哑:太师在何处?
内侍深埋着头,不敢说话。
参知政事能将朕软禁在这文德殿内,莫非还能拦着朕见岳丈么?
皇上厉喝道:叫太师来!朕要见庞太师!他的嫡女如今还是朕的皇后,莫非庞太师不要这个嫡女、两个皇子了?!
大殿安静,皇上的声音空荡荡回响,几乎显出隐隐凄厉:朕知道他庞家投了襄王!如今襄王事败,庞家能有善终?朕恕他死罪,与朕合力诛除叛臣!
皇上。
内侍打着颤,扑跪在地上:太师,太师已
皇上死死瞪了眼睛:已怎么了?!
见了政事堂明发文书那日,大皇子与二皇子出宫,去了太师府。
内侍颤声道:说要,要递投名状,同太师借项上人头一用
皇上脑中嗡的一声,狠狠一晃,脱力跌坐在龙椅上。
他忽然有些喘不上气,按住胸口,费力喘息:他们两个现在何处?
皇上艰难地粗重吸气,涩声道:叫他们来
内侍伏跪在地,还要再向下说,听见脚步声回头,脸色瞬间惨白,闭紧了嘴连滚带爬逃到一旁。
皇上喘了一刻,抬起头,看了半晌才看清眼前的两道身影。
皇长子萧泓、皇次子萧汜。
这些天禁宫内外情形莫测,这两个皇子也无疑不十分好过,神色形容都有些狼狈,萧汜的袖口还沾了隐隐泛黑的血色。
不错。
皇上压着翻腾血气,吃力笑了下:有几分朕的果决手段。
皇上稳了稳心神,尽力缓声道:庞太师勾连叛逆,其罪当诛。你二人大义灭亲,朕心甚慰
他话未说完,面前的两人却都已俯身跪了下来。
皇上脸色微变。
这两个人若不跪,他还有几分把握,此时见着两个儿子跪在眼前,心中反而腾起浓浓慌乱,撑着向后挪:你,你们
萧泓磕了个头,膝行上前,从袖中摸出了一枚玉瓶。
你们要做什么?!
皇上瞳孔骤缩:朕是你们的父皇!
父皇。萧泓避开他的视线,握了玉瓶道,为了儿臣,您该这么做
皇上胸口一片冰凉:什么?
萧朔不想当皇上,儿臣已查清了。
萧泓低低道:您若退位,最合适的不就是儿臣来继位?儿臣愿意给他们当傀儡,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儿臣绝不过问,也绝不复仇。只靠说的他们不会信,只靠外祖父的项上人头,只怕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