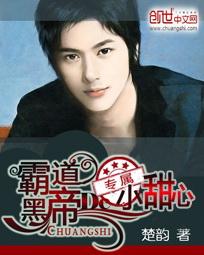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情归何处的含义 > 51 泣血的早晨(第1页)
51 泣血的早晨(第1页)
前些日子小丁听我说找了家要债公司合作很是羡慕,叮嘱我若效果好必须介绍给她,她也是一屁股债要讨呢!正好今天她打来问情况,我便将此事说给小丁听,她竟然安慰我说:“花五千就花五千吧!也许那时候你跟老马就只一线之隔了呢!”
我啐了她一口,没好气道:“那我还得谢谢他们沉着冷静、方法得当;谢谢老天佑我啦!”
说完又把自己气得一通眼晕。
心中顿时懊悔不已,找秦维刚这件事情真是搬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意味呢。
如今除了就这么搁置着,什么都做不了,我若主动对他谈终止合同,他必然又要问我讨要一笔违约金,干脆就这么搁着,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他若两头都拿不到钱,自然会偃旗息鼓。
与其说是对秦维刚的失望、更不如说是对要债公司这种模式的失望,这些一次次失望将我带入了更深的忧虑。
恍然间明白过来,这个世界之所以陷入了债务的连环套,是因为失去了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偿债能力。李天诚面对这样的压力都拿不钱来,想必是真没钱,所以还不了我;而我心心念念想还钱,兜里没有一个子儿,也还不了给霸哥和老梁;霸哥和老梁若是自有资金还好,若是借了些,也还不了给别人。我们都被悟空的定身法给定住了。再丑陋僵硬的动作也收不回来,只剩惊恐焦虑的眼珠在眼眶里转。
互害模式还在循环,六月末了,不见钱。罗仕虎又找上门来,这次可没那么大方请我“住酒店”,而是派了两个大男人“住我家”,吃我的用我的,我不想彩凤的房间被他们霸占,只得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他们霸占。屋子里莫名其妙的弥漫着汗味和烟味,出了门他们也寸步不离的跟着我。这罗仕虎从不与我约架,也不砸我东西,但却分分秒秒的折磨我、让我难堪。我后怕着,倘若是我上班那会儿,就真要命了,他们办公室里跟着你,商务谈判跟着你,那不真是要人命了。
他们不停的逼我出去借钱,不拿出钱来就这么一直跟着我,我如今哪还有地方可借啊!跟了快一星期了,一日在外面的一处女卫生间,两个跟屁虫等在门口,我发现这厕所竟然还有一处出口。便溜出去顺势坐上了一辆公交车。久违了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这辆车开往的方向正好是黎昕家。他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前几天黎妈妈还打电话叫我有空去看看她呢,可不正是真开往春天的公交车嘛!
黎妈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亲手削了梨给我吃,还一直问我的近况,留我吃晚饭呢!
在我自己家里,我妈对我太过了解,装高兴很累,装着装着她又问你:“你不欠别人钱了吧?”“不欠了!”
说着说着又问:“你身上还有钱吗?”
怕他们问着问着我便说漏了嘴,就一直说谎,还得说得符合逻辑、没有破绽,搞得我神经紧张,很是心累。
黎妈妈可不一样,她不了解,也就不问,只与我说些细碎家常,真是很久都没有这么温暖轻松了,兴奋了一小阵,正愉快吃着晚饭,有人敲门,黎妈妈开了门,两个跟屁虫进来坐下,拿了我们的碗筷就吃,黎妈妈呵斥他们这是做什么,说是要报警,他们便与黎妈妈说我欠了他们一大笔钱。
我脸上一阵阵发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对黎妈妈说了句对不起,便灰溜溜出了门。自然那两个跟屁虫也跟出来了。一路上,我怀疑他们在我身上装了定位跟踪装置。
第二日,我正发愁黎妈妈恐怕会把我欠债被人追债这件事情告诉黎昕,到时我该怎么解释!意外就发生了,黎昕心急火燎从J市赶了回来,告知我黎妈妈前晚打了电话给他,说了奇怪的话,他连夜赶回家却不见黎妈妈的踪影。
我心中莫名的咯噔了一下,为什么刚巧会是我去哪儿丢了一地的脸后就发生的呢?不会同我有什么关系吧?她老人家这是跑哪儿去了?
我心虚又着急,一夜都睡不踏实,这个时间点总让我怀疑是否是自己触发了什么机关,启动了这个事情。只能祈求老天爷让黎妈妈赶快毫发无损被找到,祈求一切都是我胡思乱想。
第三日,派出所定了失踪,警察也开始寻找。我本想去他家陪着他,一起找或者一起等消息,让他有个人好商量,但身后挂着两个跟屁虫,又没法开这口了。
第四日清晨,大约才六点,我还在床上,接到黎昕声音颤抖的电话,他告诉我,警察通知他去月湖公园认尸,我脑中一阵轰鸣,四肢颤抖的穿上衣服,没有刷牙洗脸便出门,身后传来两个跟屁虫凌乱的脚步声,这种时候,我已经顾不得黎昕发现我的真实状态了。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只听到自己在奔跑中粗重的呼吸声。
远远看到黎昕跪在地上,水边躺着刚捞上来的一个人,一块布遮住看不到脸,可身上穿的枣红色外衣和黑色裤子,正是那天下午黎妈妈穿的那身衣服。我一阵昏厥,死死的抱着一棵树,瘫坐在地上。
7月,夜雨让清晨的月湖公园清冷萧瑟,曾经的浪漫温情之地,此时因传来噩耗而变得面目狰狞。脑海里心烦意乱纠缠着不同的缘由:这究竟是真的?还是虚惊一场?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伸长脖子边走边张望着,远远看到黎昕跪在一处岸边,水边似乎刚捞上一个人,那副可怜的身躯湿漉漉斜躺在水边草坡上毫无生气,一块蓝布盖住了脸,两只脚上只穿着袜子,鞋已不知所踪。看不到脸,可那身衣服,正是那天下午黎妈妈穿的那身衣服。眼眶里一阵热浪袭来,死死抱着手边一棵大树,脚下无力缓缓瘫坐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