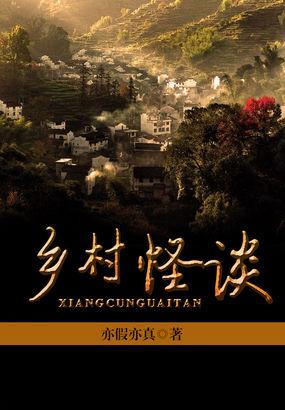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离婚才爱txt百度 > 第152页(第1页)
第152页(第1页)
没了玩笑的心思,韩晔目光定定地看向眼前的人:“你真实的想法,现在可以说了。”闻言,白臻榆眉宇舒展些,眼眸潋滟神采,他并未直言,反是似叹非叹地说了句:“白家前些年在b市洽谈成功的项目,很成功吧”“的确。”韩晔眨眨眼,随即意识到什么,嘴角噙着笑意,意味不明地附和道:“当年新开发区项目白家拿下,有很多人眼红来着。”“白臻榆,现在我是真的有点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等他与韩晔把“细枝末节”都商榷完毕,已至深夜。白臻榆只身站在路灯下,有些困倦。疲乏似乎一直是很奇怪的状态,即使人人总以“好好休息”作为抵御它的手段,可实质上两者之间的牵扯似乎并没很深。睡的昏天黑地后再度睁眼,有时也并未能好到哪里去。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过是跟心有关。白天纷杂的事情在此时作乱的频率似乎高了些,各样的神情陆续从眼前闪过。而他此刻的神情却与当时并无二致。也不知是真为旁观还是佯装得够好,以至于他看自己的心意也不真切起来。白臻榆半阖着眼,蜷起的指尖触及掌心又倏而松开。但至少有件事是对的,终止姚景不自知的折磨,对方下不了的决心,他来也一样。夜晚升腾而起的凉意一点点沁润,似乎粘湿了眼睫,略微有些戳人,于是只能掀起眼来,任由冷风将眼尾冻得恹恹泛红。——“其实你从未爱我。”虞洐的话落地应声,一阵强过一阵,直至他再也无法忽略。白臻榆觉得冷。或许虞洐说得对,他把对方当作了聊以自慰的载体。寄托着、倾注着,想要回应。回应要“真”。可这个“真”跨越时间空间,长途跋涉,他要完美、一丝不苟、全数贴合心意。太难。他愿意去想虞洐所言结果是对的。至少这样,当年与现在就未完全算清并且永远算不清。他愿意固执地如对方说的,把两个节点的同一人一分为二,这是最心安理得,最好放手的方式,是虞洐替他做的决定,给的“出口”。以此,他能保留记忆里最好的那部分,再把其余的心无负担地扔掉,他们只不过是陌生人。可是人自欺欺人时如何努力劝说自己心安理得呢给出这种说法的虞洐,和当年那个巷口坦然打量他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那时他狼狈,跌在泥里,最不堪。自尊是死死咬住唇舌的不求饶,也不止是。毕竟他目光不移地盯住巷口,即使血糊住视线,从始至终都不是为了求救。面对那样的他,怜悯与同情应当会毫不保留地给予出来,再履行救世主的工作,救他出水火。大部分人会是如此。即使这样的想象,连词句的描述都令他羞赧。所以虞洐才如此特别。对方看向他的眼神什么也没有,仿若仅仅是一次再直白不过地打量,即使他不堪裸露,落在对方的眼里,只不过是白臻榆。和穿好制服接受荣誉的白臻榆没任何不同。那时他太年轻,只明白心间微微地一动却时至今日的涟漪未停到底代表什么,所以铭记,千思万想。之后偶尔年纪稍长,所学变杂,隐约明白了那刻所隐含的是什么。虞洐没有“救”他,对方只是亲身走进泥潭深渊,以同等的姿态看向他、牵着他,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因为同样身陷囹圄,便不存在高高在上地凝视与从上至下的同情。白臻榆垂落眼睑,从思绪里渐渐抽出神来。他不再站在路边等,而是向前迈开步子。或许找到出口。-------------------------------------家政阿姨的联系电话打到他这来时,虞洐正在开会,看到陌生号码他的第一反应是挂断,可莫名他犹豫了一瞬,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显示通话中了。同在场的人说了声抱歉,虞洐走到外面,听见那声清清楚楚的虞洐先生。是认识的人。“您是?”他没走太远,背抵住墙,控制着声量。那边似乎信号不太好,说话断断续续:“不好意思打扰您了但白白先生不接电话,我又实在不敢自己决定。”从旁人嘴里听见白臻榆名字,令虞洐稍稍愣神:“有事您说。”“我见平日里紧闭的侧卧开着,想问问您是想要我打扫么?主要您说过这个房间不用管,您自己会解决的”侧卧是他的房间么?脑海里迅速闪过些什么,虞洐鼻尖似乎掠过一丝薰衣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