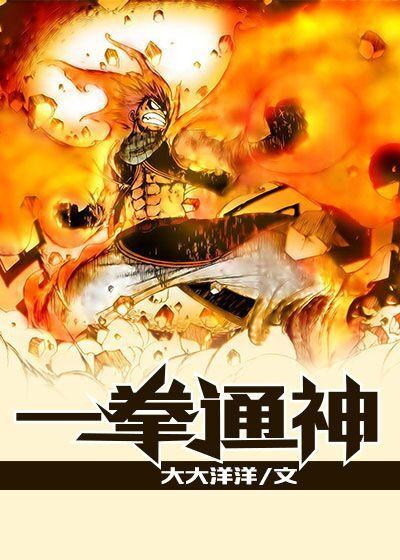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离婚才爱txt百度 > 第124页(第1页)
第124页(第1页)
眼尾恹恹下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声线:“虞洐,你还不离开吗?”闻声虞洐眉睫颤了颤,张合着嘴,终于挤出来一句话:“会的。”随即他侧过身,脚步却未移动,停了半晌:“你学校的事我很抱歉。现在已经解决了,只要你愿意,可以回去继续”他抿唇,仔细斟酌着词句,以免把不好的事情不经白臻榆允许透露出来。他顾忌着姚景在场,要求和白臻榆单独谈,想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想这些本不该让对方经历的难堪、不会再泄露分毫。可其实想想,白臻榆少有的不体面,几乎都由他一手造就。“罪魁祸首”为自己亲手促成的苦果瞻前顾后,只会更像虚情假意。虞洐微地怔神,话语径直断成半截。“够了,虞洐。”,兀地抬眸与人直视,白臻榆眉眼挑起抹弧度,冷笑出声,“回去?”“你们真的太有意思了是,左右不过是说一句的事,权势金钱被堆在力量的金字塔尖,做什么事都丝毫不费力气,即使天翻地覆也没关系,总是想着可以补救。”白臻榆少有如此情绪起伏的时刻,虞洐僵硬地站在原地,没有转身。“可凭什么呢?”,白臻榆下颌绷紧,好似把锐不可当的锋刃,要鲜血淋漓才罢休,“补救让局面恢复如初,所有的溃败、崩塌、伤害,就可以统统一笔勾销当不存在么?”他攥紧拳,此刻才是真的无所顾忌:“补救和挽回一样,都不过是自以为是的付出、觉得凡事可抵消的傲慢罢了。”他白臻榆不接受,也不会接受。虞洐终于转过身来。白臻榆看着眼前的人——所有放浪形骸都老老实实地被关押进躯壳里,倦怠和疲惫好像第一次在虞洐的脸上如此分明。他像是永远奔驰向远的列车,风景必定只能是途径,所以眉眼中永远藏着玩世不恭的戏谑,像是没什么能被他放在心上,也就没什么值得让他耗费几分心神,自然也不会为任何事物羁绊。故而永远向前。但此刻的虞洐仿若奔流的水遇到寒雪漫天,马上便会凝固。虞洐出声才觉察自己嗓音沙哑,习惯性笑了笑,想把话续下去,只是抵御那些字句似乎比他想象的要更花力气,锥心似的让人闭嘴。所以能说的话也就只剩下告别。若他不是蠢货,就该明白之后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不是白臻榆没留给他,而是他的懦弱和退却堵死了它。补救,的确荒谬。两字轻巧地念出来,明明最多只是“亡羊补牢”的无功无过,平白无故地紧贴上“救”,仿佛意味就变了——象征天神降临地相助,能值得人叩拜感谢。但就像白臻榆问的,凭什么呢?他亲手推开的,他选择的,结果就必然是他该承受的。看吧,他早就说过,白臻榆这人不可招惹,会冻人骨头而他饥寒交迫,偏要一次次试探,看清冰中淬火,却也死生一线。-------------------------------------白臻榆晃神只是一瞬。他义正辞严,几乎快要把自己哄相信了走不出前尘往事的是他,望见虞洐时还会回忆的是他,“补救”的也是他。因为当时错过形成的遗憾,好比拼图所缺的最后一块,他想替当年的自己睁开眼睛,可忘了,今时替往日做事,他还是拉不住人。于是计划着扯平,也就可以把经年累月联系的“感谢”吞咽下去,隐藏掉他愚蠢的“补救”,也遮掩住他嘲弄的“天真”。白臻榆垂下眼睑,阴影笼在他出挑的五官上,看不清神情。姚景咬唇打量,可“潘多拉魔盒”总是不容易关上的,哪怕天时地利人和全无,注定不合时宜。还是要说。哪怕错误抉择,但起码选择过。“臻榆”白臻榆掀起眼,语气隐隐急切:“姚景,我很累了。”“臻榆,你知道我会说什么的,是么?”姚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声量几不可闻。白臻榆不由自主地叹息。“这么多年好友,我不知道你有自欺欺人的毛病。”,姚景想让自己显得尽量轻松些,只是心口翻涌苦意,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样从容,“既然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的话,你何必拦我?”“姚景”,白臻榆为难地皱紧眉,“你也说了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友”姚景低低地笑出声,伸手挡住了眼睛:“臻榆,可我不止希望当好友。”“我一定要说、说出口。”成全我吧。后半句,姚景没说,他沉默地看着白臻榆,这数年来,他从未这样平静地注视白臻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