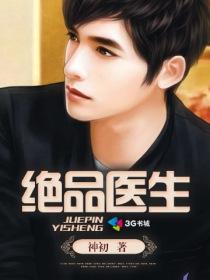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哭泣的骆驼全文免费阅读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运气就有那么不好,我又回军营里买菜的第一天,那个军曹就跨着马靴大步的走进来了,我咬着嘴唇紧张的望着他,他对我点点头,说一声:&ldo;日安!&rdo;就到柜台上去了。
对于一个如此不喜欢沙哈拉威人的人,我将他解释成&ldo;种族歧视&rdo;,也懒得再去理他了,站在他旁边,我专心向小兵说我要买的菜,不再去望他。
等我付钱时,我发觉旁边这个军曹翻起袖子的手臂上,居然刻了一大排纹身刺花,深蓝色的俗气情人鸡心下面,又刺了一排中号的字‐‐&ldo;奥地利的唐璜&rdo;。
我奇怪得很,因为我本来以为刺花的鸡心下面一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想不到却是个男人的。
&ldo;喂!&lso;奥地利的唐璜&rso;是谁?是什么意思?&rdo;
等那个军曹走了,我就问柜台上沙漠军团的小兵。&ldo;啊!那是沙漠军团从前一个营区的名字。&rdo;
&ldo;不是人吗?&rdo;
&ldo;是历史上加洛斯一世时的一个人名,那时候奥地利跟西班牙还是不分的,后来军团用这名字做了一个营区的称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rdo;
&ldo;可是,刚刚那个军曹,他把这些字都刻在手臂上哪!&rdo;
我摇了摇头,拿着找回来的钱,走出福利社的大门去。在福利社的门口,想不到那个军曹在等我,他看见了我,头一低,跟着我大步走了几步,才说:&ldo;那天晚上谢谢你和你先生。&rdo;
&ldo;什么事?&rdo;我不解的问他。
&ldo;你们送我回去,我‐‐喝醉了。&rdo;
&ldo;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rdo;
这个人真奇怪,突然来谢我一件我已忘记了的事情,上次他送我回去时怎么不谢呢?
&ldo;请问你,为什么沙哈拉威人谣传你恨他们?&rdo;我十分鲁莽的问他。
&ldo;我是恨。&rdo;他盯住我看着,而他如此直接的回答使我仍然吃了一惊。
&ldo;这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并不是那一个民族特别的坏。&rdo;我天真的在讲一句每一个人都会讲的话。
军曹的眼光掠向那一大群在沙地上蹲着的沙哈拉威人,脸色又一度专注得那么吓人起来,好似他无由的仇恨在燃烧着他似的可怖。我停住了自己无聊的话,呆呆的看着他。
他过了几秒钟才醒过来,对我重重的点了一下头,就大步的走开去。
这个刺花的军曹,还是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手臂,却刻着一整个营区的名称,而这为什么又是好久以前的一个营区呢?
有一天,我们的沙哈拉威朋友阿里请我们到离镇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阿里的父亲住在那儿的一个大帐篷里,阿里在镇上开计程车,也只有周末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阿里父母住的地方叫&ldo;魅赛也&rdo;,可能在千万年前是一条宽阔的河,后来枯干了,两岸成了大峡谷似的断岩,中间河床的部份有几棵椰子树,有一汪泉水不断的流着,是一个极小的沙漠绿洲。这样辽阔的地方,又有这么好的淡水,却只住了几个帐篷的居民,令我十分不解。在黄昏的凉风下,我们与阿里的父亲坐在帐篷外,老人悠闲的吸着长烟斗,红色的断崖在晚霞里分外雄壮,天边第一颗星孤伶伶的升起了。
阿里的母亲捧着一大盘&ldo;古斯格&rdo;和浓浓的甜茶上来给我们吃。
我用手捏着&ldo;古斯格&rdo;把它们做成一个灰灰的面粉团放到口里去,在这样的景色下,坐在地上吃沙漠人的食物才相称。
&ldo;这么好的地方,又有泉水,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住呢?&rdo;我奇怪的问着老人。
&ldo;以前是热闹过的,所以这片地方才有名字,叫做&lso;魅赛也&rso;,后来那件惨案发生,旧住着的人都走了,新的当然不肯再搬来,只余下我们这几家在这里硬撑着。&rdo;
&ldo;什么惨案?我怎么不知道?是骆驼瘟死了吗?&rdo;我追问着老人。
老人望了我一眼,吸着烟,心神好似突然不在了似的望着远方。
&ldo;杀!杀人!血流得当时这泉水都不再有人敢喝。&rdo;&ldo;谁杀谁?什么事?&rdo;我禁不住向荷西靠过去,老人的声音十分神秘恐怖,夜,突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