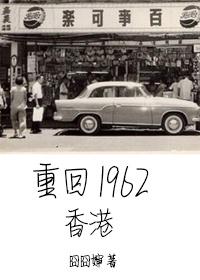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陌上行歌曲 > 第十一章116东倭国是十九(第1页)
第十一章116东倭国是十九(第1页)
在袁澜同二丫说话的时候,明州海商方斫正在向商成作礼,可谢座谢茶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陡然间便异变突起。事情来得太快,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既谦卑又恭敬的笑容也登时冻结在脸,扎煞着双手微屈着两条腿立在石凳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没胆量开口说句劝解的话,目光死死地瞪住眼前被打磨得光滑平整的石桌,连眼珠子都不敢稍微错动一下……屏息静气之间忽然想起听说过的对商成的风评物议,冷汗刷地一下子就从额头颈项间冒出来!
袁澜更是面se如土,手脚都不知道该朝哪里放了,干张着嘴却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现在的问题不是他说错了话办砸了事,而是他的四弟根本就不在京城。他四弟前年就被他差去泉州打理买卖,眼下已经在那边呆了两年有余,商成的侍卫在商号里找不见人,必定会去打听,等到商成知道了真相,事情才真正是无可挽救了。他现在懊悔得不得了,恨不能找来针线把嘴巴缝起来!来之前他二弟袁池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见到商成就认错道歉,以商成的爽朗豁达xing情,肯定不会与他计较。袁池还再三地告诫他,见到商成就好,什么事都与商成说便是,千万切记不要节外生枝。结果他还是没能管束住自己,来就和二丫说话,结果就铸成了大错!
商成已经下了逐客令,可袁澜却不能走。他心头明白,要是真走了,以前结下的那点香火情分就会荡然无存,以后再也别想走进应伯府的门。至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遭际,他根本就顾不思量也不敢去想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哪怕磕头赔礼也得让商成回心转意!
袁澜赖着不动脚步,老刀也不过来撵他,只是拿刀子一样凌厉的目光下来回地打量他。老刀虽然沉默寡言,心思却很缜密,跟在商成身边的时间又长,商成说话做事的一些习惯他都很清楚。商成虽然对袁澜不假辞se,话也说得重,但手里的茶盏一直都没放下,也没掉头去和二丫说话,这些细节都说明,商成其实也就是吓唬一下袁澜而已。这样的事情商成在燕山就做过不少回;象孙奂、钱老三还有邵川郑七他们,几场胜仗打下来,一个个骄横得都快不记得自己到底姓什么,尾巴全都翘到了天,看什么都不顺眼,嘴巴一张就是“狗屁”,要不借着机会经常踢几脚骂几句的话,早晚要捅出篓子。商成身边的侍卫,基本都配合着商成打杀过孙奂他们的嚣张气焰,因此做这种事情是驾轻就熟。既然商成不过是想敲打一下姓袁的,老刀也就没有认真动手赶人,只是摆了个凶狠的架势跟着装腔作势罢了。
但是,袁澜并不是孙奂和钱老三。孙奂和钱老三他们都是被商成打骂惯了的人,这边被骂得狗血淋头,缩头耷脑地屁都不敢放一个,转过身就权当是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象范全姬正这些老燕山,哪怕商成挨着个把他们喷一脸的唾沫星子,也还是嬉皮笑脸的无赖模样,经常倒把商成闹得哭笑不得。和他们相比,袁澜就差远了。商成一摆脸se,他就被吓得两条腿打颤;商成口气稍微重一点,他就连低头认错的胆量也没有了;再加老刀恶狠狠地站在一旁,他就只顾着拿眼睛朝地看,大约是想寻一块干净的地方跪地求饶……
商成还是绷着个脸,端着茶盏看也不看袁澜。其实他也有点傻眼。这才多大点的事?拱下手打个哈哈就过去了的,怎么袁澜的脸全然是一付如丧考妣的模样了?这家伙以前不是这样啊,当年跟王义斗法的时候,就算逃难也是一路有说有笑,怎么一转眼就经不住恐吓了?
眼看着袁澜便要做出点出格的事情,商成就赶紧给二丫递眼se: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二丫开口替袁澜求情,他就可以就坡下驴了。
可二丫脸红红的,低着头根本没看他。商成围护了她,她正开心高兴得不得了,哪里有心思去理会别的事情……
二丫指望不,商成就只能靠明州大海商方斫,但眼角余光扫过去,大海商还在扎着马步……他正盘算着如何才能不露声se地缓和一下气氛,就看见蒋抟从桃林间的小径走过来。
几天前,蒋抟已经在工部报到,接领了差事。刚刚到任,乍一了解情况,他就叫苦连天。工部起的那些白酒作坊,人事混乱财物混淆的毛病就不说了,各种章程千疮百孔四面八方到处漏风也不提了,单是一个作坊中吃闲饭的比干事的人还多的毛病,就让他恨不能马递出辞呈。他本来打算,在家眷没到之前,就先在商成这里搭伙,结果接手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场,这几天光是看卷宗就要熬到半夜,实在是没时间也没jing力再在商家庄子和衙门之间来回跑,干脆就住到商成在城里的府邸里。眼下事情总算稍微有了的眉目,明天又是休沐,他才抽空过来找商成拉话。
蒋抟远远地就跟商成打了招呼,走到亭边才发现站着的人居然是自己的熟人,便笑着拱了拱手,说道:“这不是半山兄吗?自从燕州一别,到现在也有个半chun秋了,你怎么也来了?”说着,也不停下脚步,就坐到二丫给他让出的石凳。他和霍士其是平辈论交道,月儿二丫他们平时也都是尊他一声“蒋先生”的,因此并不怎么和她客气讲礼。等二丫给他斟茶汤,道了谢之后,这才又对袁澜说:“你站着干什么,怎么不坐下说话?你和督帅也不是头回见面,以前可没见你这样拘束。来,坐了说话。”又说,“你可是比去年秋天时很胖了一些。来,坐下和我说说,这怎么作养身体才能有个体面富态。”
袁澜心里清楚,这人是把自己错认成了叔伯兄弟袁池。他不知道蒋抟是谁,但看蒋抟和商成如此亲近,也知道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只要这人肯出言搭救,商成多半不会再追究自己的差错。按他本来的xing情,当然是附和着蒋抟的话就势便向商成告饶,可他刚刚才因为话多吃了苦头,这时候就有点放不开手脚。正在犹豫迟疑,就听商成说:“老蒋,你认错人了。这不是袁澜袁半山,是他的叔伯兄袁澜袁观波。”转过脸对袁澜说道,“你也坐。一一老方也坐下。看你这架势,我都替你难受。”又对袁澜说,“你可真是好运道。前头遭难时有人帮着你,今天又有人帮着你,怪不得你们家的买卖越做越红火。”
袁澜终究不是愚笨人,商成话里的jing告他能听懂,揶揄的意味也明白。他心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连冷汗都不顾不擦,赶紧过去郑重地向二丫道歉,并且再三声明,那天说的想参股的话绝对不假,五万缗制钱也已经备下,只是因为五十多万斤的铜钱来往运送极不方便,所以先贮在城里的商号里。二丫随时都可以派人去清点查验。
蒋抟这几天都在衙门里忙碌,还没听说五万缗的事,就好奇地向商成打问。
商成给大家的盏里倒着茶汤,随口说道:“老袁想在我搞的那几样航海技术里参一股。”
“五万缗折算一股?”蒋抟问。
商成点了下头。
“是指你做的那些指南针和海舆图?”
“就是那些。”商成说,“还有个地球仪。”
蒋抟没言声。他低着头,慢慢地呷了两口水,才唆着牙花子说:“卖便宜了。”他知道袁澜是商成的布衣患难之交,情谊不同寻常;姓方的虽然不清楚来路,但既然能和袁澜同道,想来交情也非浅薄,也就不再忌讳什么,又说道,“我前两天看过那份《乞除专利钱与燕山屹县霍氏疏》。这分奏疏还没下发到各地,也没刊载在邸报,所以民间暂时并不知闻,也没有什么反响。但请督帅留意了,这份《乞除专利钱与燕山屹县霍氏疏》是开天辟地的新举措,其震荡之深远,当不啻汉武帝时的盐铁专营。据我所知,眼下朝廷把这个口子一开,有霍氏白酒的先例在前,接下来工部便有不少的事项要请专利钱,象苏州的叠绣技艺,还有漳绒的技艺,这些都是要请专利的。等民间琢磨出其中三昧,只怕向朝廷请专利钱的会蜂拥而来。如您所做的这几样航海所用的物件,舆图和地球仪暂且不题,单单是个指南针,效用广泛难以历数,其中的利益更是累千累万。五万缗一股实在是太低了。只在指南针一样就已经低了!”
商成自然很清楚指南针、地球仪和世界地图这三样东西的真正价值,但他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常秀的《乞除专利钱与燕山屹县霍氏疏》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现在听到蒋抟的判断,当真有一些振聋发聩的感觉。他的见识比蒋抟多,眼光也更加长远,对专利的实施和落实之后将引起的变化自然也更加清楚,思量着其中的种种利弊得失,一时间就忘记了说话。
蒋抟说,民间对专利钱的认识会比较迟钝,这显然不是事实。亭坐着的袁澜和方斫就很敏感。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听说了两桩大事。一是朝廷准许屹县霍氏拥有白酒专利钱并非特例,他们这些商贾也是可以向朝廷申领专利钱;二是商燕山搞的航海技艺并非镜中花水中月,至少其中一样名为“指南针”的已经做出了实物,而且是“利益累千累万”的实物!本意原不在此的方斫,更是激动得眼中放光。他们方家从中唐就开始做海商,高丽、东倭、大越和真腊的海路都很熟悉,深知海行走最难的不是躲避风浪,而是一张张凝聚了无数心血的海舆图。从中唐到现在两百余年,花在海的金银不知道有多少,死在海的方家人也不知道有凡几,可海道也只开辟到南天竺;从南天竺再向西的诸如波斯、大食、大秦、埃里和黑山昆仑等国,从来都没有到过。焉知这应县伯府里就没有他们渴盼百年的海舆图?更何况还有个指南针。海往来的舟船一般都是成群结队,为了在茫茫大海指引方向,当首的船都备有司南。但司南一来保管不易,二来也不甚准确,海风浪颠簸地秤不能平衡,因此司南也时常有误指,抵达时差谬个十数里数十里极其平常,既然蒋抟敢夸下海口,想来指南针定比司南可靠十倍百倍……
他还在思谋,袁澜却在瞬间就拿定主意。他们袁家早就想下海了,可手里没有海舆图,什么事都要看方斫这样的大海商的眼se,处处都要担心别人的掣肘,心头总是不得安稳。眼下忽然有了个出海的机会,那还多想什么?不管了,反之铜钱放在那里也不能生子,五万缗一股,他们入了!哪怕再添十万贯,他们袁家也绝不皱一下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