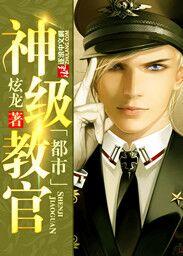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犯罪团伙扎针逃避追捕是为什么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他看了一眼手表,惊叫一声。
“我必须得走了。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们两位。改天我们在伦敦一起痛快喝一杯,再见。”
他急匆匆地走了,这时一个侍者手托一个浅托盘送来一页便签,上面没有署名。
“这是给您的,先生,”他对汤米说,“吉尔达·格兰小姐让送的。”
汤米好奇地撕开,信封内页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您或许能帮帮我。您将要走那条路去火车站,那么您能在六点十分去一趟摩根大道旁边的白房子吗?
您真诚的,
吉尔达·格兰
汤米对着这页纸点点头,侍者走后,他把这个便签递给了塔彭丝。“这太奇怪了,”塔彭丝说,“难道是因为她还认为你是神父吗?”“不是,”汤米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应该是因为她最终明白我不是神父。喂,这是什么?”
汤米口中的“这”是一个年轻人,一头火红的头发,桀骜不驯的下巴,穿着一身极为破旧的衣服。他已走进房间,向他们走来,嘴里自言自语。
“活见鬼了!”这个红发男人用力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正是——活见鬼!”
他扑通一下坐在这对年轻夫妇旁边的椅子上,十分不高兴地盯着他们。
“所有女人都该见鬼去,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年轻人说,狠狠地看着塔彭丝,“哦!只要不高兴就把我踢到街上。把我赶出酒店,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出我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抑制自己的情感,我们为什么非得傻笑,说着和别人一样的话?我并不认为这样讨人喜欢,这样就是彬彬有礼。我觉得这就像是扼住了某人的喉咙,慢慢地让他窒息而死。”
他住了嘴。
“这话是针对某个人?”塔彭丝问,“还是所有人?”
“某个人。”这个年轻人冷酷地说。
“有趣,”塔彭丝说,“你愿意给我们讲得更详细点吗?”
“我的名字叫赖利,”这个红头发男人说,“詹姆斯·赖利。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写过一部宣传和平主义的诗集——写得不错,不自夸地说。”
“和平主义诗歌?”塔彭丝吃惊地说。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赖利挑衅地问。
“哦!没什么。”塔彭丝赶紧说。
“我一直向往和平,”赖利恶狠狠地说,“让战争和女人下地狱吧!女人!你看到刚才在这儿晃荡的那个女人了吧?她自称吉尔达·格兰。吉尔达·格兰!哼!我曾是那么仰慕她。我对你们说——如果她还有颗心,就应该感受到我的情感。她曾经喜欢过我,我一定还能赢得她的芳心。如果她把自己卖给那堆臭粪,勒康伯里——哼,我会立刻亲手杀了她!愿上帝保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