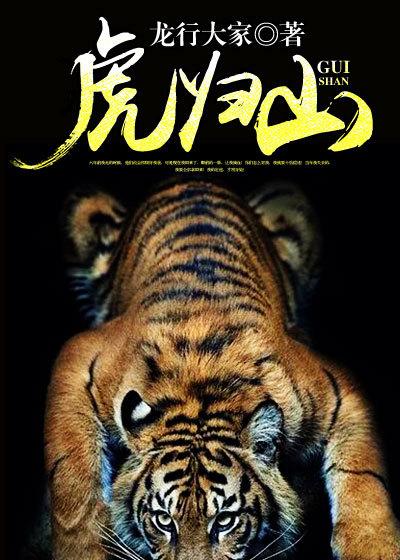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退婚后侯爷他打脸了讲什么故事 > 第113章(第1页)
第113章(第1页)
沈惊晚看着谢彦辞通红的双目,笑着摇了摇头,一字一句的同他说的清清楚楚:“你把愧疚和爱混淆了。”
谢彦辞道:“我这次很清楚明白。”
沈惊晚笑的很是淡然,语气中含着轻松,好像过往尘事,早已烟消云散。
那些爱啊,恨啊,都不重要了。
她语调很柔和,带着从来没有过的冷静,一如当年的谢彦辞:“可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才是最轻松的时候,我们只要顾着自己就好,不必将心分担出去。爱来爱去,到最后才明白,只有不爱的时候最快乐,谢小侯珍重,日后不必惦念。”
这次没再等谢彦辞说些挽留的话,转身就走了,走的很决绝利落。
谢彦辞忽然失去了大半的气力。
她说,现在最开心。
可是他却一丁点都感觉不到快乐,心好像被掏空,那个发了春芽儿的深处,还未曾来得及长大,就已经枯亡。
他站在原地,老僧入定般,看着沈惊晚渐行渐远的背影,一如多年前的她。
这么好的天气里,他忽然觉得全身刺骨寒。
若是她当真开心的话,不原谅他——也好。
沈惊晚走到国公府门前,鞋底带起灰尘。
沈延远放下环抱的胳膊,看向沈惊晚,二人转身朝着府中走,沈惊晚嘴角的笑挂起,看上去似乎并无什么事发生。
沈延远起了好奇心,问道:“你说什么了,我瞧着你们两个的面色可是截然不同。”
沈惊晚那笑仍甜甜的挂着,没心没肺的道:“谢小侯只是问问家中可好,我说都好,许是还惦记那次一事吧。”
语罢,也就不给沈延远继续追问的机会,提着裙摆跨过耳门,直接朝着自己院子走去了。
背过身的瞬间,她的笑意才悉数散去,心里只觉得抽痛,像伤口被盐水腌过一般,疼的发麻。
-
次日清早,燕君安来了国公府,来时还带了些东西,交由下人手中。
卫国公只当他是来找沈延远的,笑着道:“远儿早上出门有些早。”
“我是专程来找国公爷您的。”
燕君安开口道。
卫国公愣在原地,看向燕君安疑惑道:“找我?”
见愿君安没有开玩笑,卫国公思索了片刻,冲下人道:“看茶。”
二人相对而坐,下人在一旁沏着茶水,卫国公笑道:“燕先生找我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