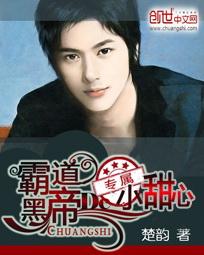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庶女的日常TXT > 第1章 楔子(第1页)
第1章 楔子(第1页)
峰叠翠秀,迷障山,水月庵,一处独门小院。
眼前的观音大士像已描好了轮廓,她一肘支在绣架上,手里捏着针,眼神空茫,半晌,轻轻叹了口气。
光透过窗棂洒落,浅淡的影子交织成绵密的网。
院门“哐当”一声,惊醒了她。
“师姐!”一个俏生生的光头小尼姑惊惶不安地跑进来。
她心里一紧,“你这是怎么了?”赶紧过去扶住,扶着师妹让她靠在禅椅上,探手推开窗户往外看了一眼,随即大步走了出去利索地关了院门,又上了门闩。
回到屋里,小师妹扑到她身上,“师姐,怎么办?师姐,她们、她们……”话未出口,眼眶已红了。
她轻声喝道,“慌什么!镇定些,你去哪儿了?”拉着师妹的手想要给她搓一搓暖一暖,才发现她手心里全是汗。
“……我、我去找空圆师姐说话,她那儿忙,叫我帮帮她,我就多待了会儿,后来我看日头不早了,就出来了,谁知道新来的那几个也去领衣裳,她们就拦着我问我多大了,说什么标致不标致的,还、还摸我的脸,呜呜——”
她脸都白了,“明镜!不是早叫你躲着她们?”
明镜哭了几声,哽咽道,“是躲着来着……”
她安抚地给明镜擦擦脸,“好了,不哭了,跟我细说说怎么回事?”
“那会儿……我正跟空圆师姐说话,听见院子外头嘻嘻哈哈的,我想着与其被她们堵在屋里,不如赶紧躲开,”明镜一边回忆,一边拧着自己的袖口,“就去了屋子后头,等她们进了屋,我就赶紧沿着墙根跑出来了,头都不敢抬,好歹快走到门口了,空圆师姐突然叫了我一声,然后她们就……”
她面露异色,“空圆?”
明镜茫然的点了点头,见师姐脸色越来越难看,她心头犹如一道闪电划过,一下子就明白过来:“空圆她、她故意的!”
两人犹如被定住了一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俱是不可置信。
空圆?怎么可能呢?那个清清静静,莲花一样的空圆!
她突然间就失却了力气。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明镜眼泪扑簌簌的掉。
看着小师妹哭泣的面孔,她心底也疼,搂过来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师姐,我们怎么办——”
她闭目深吸了一口气,给小师妹擦擦脸上的泪水,决然道,“这里不能再待了,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里,今天夜里就走。”
明镜胡乱点了点头,怔了一会儿,“那、咱们怎么出去?山上山下的路都走不得了……”
“……后山那处长了棵白果树的山崖,我带你去拾过果子的,我们用绳子缒下去!”看着师妹苍白的小脸,她定了定心,“那山崖底下有条小路,是山中猎户常走的,等下了山,咱们妆成和尚,去港口搭船。”
“那……咱们去哪儿?”
去哪儿?回家?也不知父亲还在不在泉州,即便去了,嫡母能让她进门吗?万一再把她送回来呢?父亲若是愿意管她,当初她也不至于被送出来了。
“去哪里都比留在这贼窟淫窝里强,我们早就该离开的,”她强打起精神,“咱们去——去京城。”
这些日子,逃跑的念头在她心里不知过了多少遍,时机,路线,如何乔装,心中一直胆怯,现在却是不得不走了。
明镜有些茫然,“回京城?”
她暗暗叹了口气,“别怕,总有出路的,我们干干净净的女孩儿,再怎么也不能像她们那样。”
明镜想起这半年来庵里的变化,想起前几日和师姐去后山采茶时撞见的腌臜事,不由打了个寒噤,点了点头,目光渐渐坚定。
她拍拍师妹的手,“别怕。”起身收拾包袱。
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庶女,从小没了生母,父亲忽视,嫡母漠视,倒是兄姐对她还不错,身边服侍的养娘对她也尽心尽意,冷不着饿不着,日子过得不算好亦不算坏。
十岁时的一场重病,她被嫡母舍到了空门里,说要着借这“佛门净地”养好身体,若是她与佛门无缘,十年后等她二十岁的时候就接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