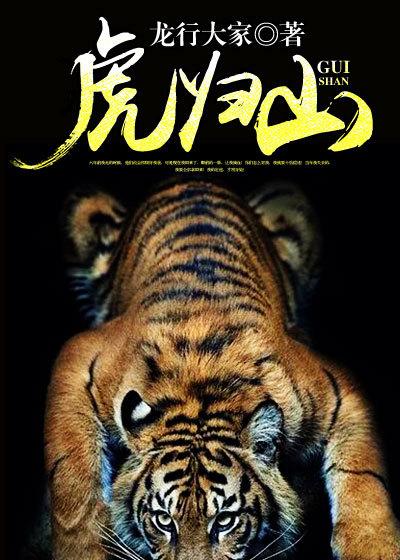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缠绵不止免费 > 爱永殇(第2页)
爱永殇(第2页)
仍清晰的记得那个傍晚,他从最好的朋友的墓地回来,手里犹捏着枯萎了的白色雏菊。
撕裂的夕阳罩着漫无天际的朦胧雾气,在眼前渐渐的模糊起来,仿佛来自那个世界的哭泣,是不舍,是遗憾,是无法改变命运碾压的呐喊。
他抬起头,看不到光明,黑色的森林陷入上笼的黑暗,将他的灵魂也一并吞噬。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正要起身离开,突然听见一串清脆的铃声,他的世界不喜欢被打扰,皱眉,戴上鸭舌帽。
铃声很快的近了,一个女孩骑着台深绿色的自行车自林中穿行而来,似乎没看见这里坐了人,径自在小广场上停下,支好车子,她拎着手里的大包欢快的跑向鸽子群,鸽子不怕人,呼的一下围笼了她。
她在包里翻找了好一会,似乎没找到想要的东西,索性提着两角,哗啦一声,里面乱七八糟的破烂堆了一地。
相片,唇彩,口香糖,书,甚至还有半个没吃完的面包,封在口袋里,被啃得惨不忍睹。
终于,眼睛一亮,拿起一个小纸袋,然后从里面倒出一些鸽食,不急不慢的,一点点的撒在广场上,鸽子们争相啄食,乱成一团,她站在那里笑,她笑的时候有两只深深的大酒窝,白的几乎透明的手指掩着嘴,鸽食一不小心就撒出一点,又惹来一顿争抢。
她站了许久,似乎发现有目光一直在盯着她,回过头,就看见长椅上竟然坐着个人,戴着帽子,面貎不甚清楚,只是那轮廓看起来倒像个英俊的男子。
她先是一愣,然后冲着他璀然一笑,眼角弯弯,酒窝深陷,正巧她的身后,一群鸽子振翅飞起,圣洁的白色做了她的背影,血染的天暮是她的画卷,满眼无边的暮色却不及她发光般的一笑。
叶湛想,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笑容,她似一朵洁白的荷,在他几近干涸的土地上冒然的开出花来,先是一朵,然后便连成一片,有风吹来,荷香阵阵。
他从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是在这个白鸽翱翔,青草依依的傍晚,他荒废的灵魂遇到了怦然心动的邂逅,这一动,竟然便是一生。
还记得那时,他告诉她,当初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你信吗?
她脸上的表情,自然是不信的,她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个平凡的傍晚,一个男人的心就此牵系于她,经过数个昼夜,经过别样年华,为了她,坠落沉沦,不择手段。
她恨他,是爱极了的恨。
他爱她,是爱极了的爱。
她说:“阿湛,我们不要走了,好不好?”
他那时,多想陪着她留在那个小岛,可是,他不能,他骗了她,他说,以后,你想来,我们随时飞过来,原来这个随时已成了永别。
在此生不多的岁月里,他已经永失了她,像是旋转木马,他与她,彼此知道彼此的存在,可是中间隔着一段距离,那是永远追逐不上,与停止不下的距离。
她说:“阿湛,你要乖乖吃药,要不然会长兔耳朵。”
她说:“阿湛,你背我好不好,我走不动了。”
她说:“阿湛,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
纤长的指掩了脸,骨节分明的指缝下,有水光一样的东西缓缓滑落。
她最后说:“阿湛,你爱过我吗?”
原来,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哭过,不是不想哭,而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触动他的眼泪。
他轻启了唇,补给她一个迟到的回答。
他说:“我爱你,很爱,很爱。”
一滴泪带着温度与悲凉,还有无边的永殇与绝望从唇边滑落,将那一声回答悉数包容,落进尘埃,消失不见。
夕阳西下,暮色渐起。
有轻轻的风声滑过,没有人听到,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有一个男人,失声呜咽。
*********
s市,某小镇。
萧暮优走进街头的照相馆,年轻的老板从游戏里懒懒的抬起头问:“照相?”
她站在门口,声音很小:“这里招人吗?”
他直起半个身子,打量着她,目光最后定格在她隆起的肚子上,咽了口唾沫:“你是孕妇?”
她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转身离开:“对不起,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