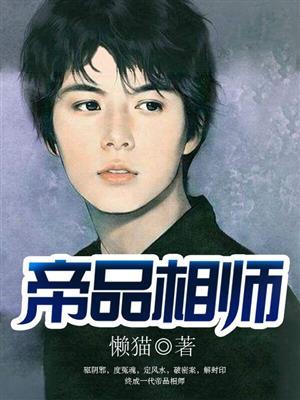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唐门密室落难的老头 > 第36页(第1页)
第36页(第1页)
他正打算发怒,想了想跟死心眼斗气又不值得,便曲线救国,在宽大的青色袍子里摸索一阵,说,“贤孙,来根烟?”唐缈伸手接过:“哟,财主啊,还抽黄鹤楼啊,你哪来的钱?”“无量天尊,做道场主人家给的,其实我也算个医生呐。”司徒湖山说,“人也真怪,好好的药不吃,偏偏喜欢喝符水,我在符水里溶了半颗阿司匹林,那人烧就退了,后来我狠敲了他们一笔。你想不想跟我学驱鬼?简单易学,道理清晰,一本万利,只要你拿解药来换。”唐缈击节称赞其可谓古往今来聪慧之胶着之二大雨在即,乌云沉沉地压在半山腰,客堂内没有点灯,十分幽暗,山风从敞开的大门吹进来,带来浓重的湿意,一如这屋里的气氛。唐缈和淳于扬并排坐在长凳上,中间隔着唐画。两人小声争论的话题毫无意义,归纳起来就是“你找不到对象”“呸呸呸童言无忌”“你几岁生的唐画”“啊呸呸呸老子没进过妇产科”之类。总算淳于扬问:“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唐缈原本肤色极白,挨了几拳后眼角就像开了染铺,有好大一块淤血。他倒是天赋异禀,被打成这样居然也不难看。唐缈向离离所在的方向使了个眼色:“妇女主任打的。”淳于扬冷笑:“活该!”“我原本是能躲开的。”唐缈略微抬起脚,“这可不是刚被你收拾了一顿,行动不便嘛。你看看这还不到一天的工夫,我身上添了多少伤了。”淳于扬问:“怪谁呢?”唐缈仰头想了想说:“呃……好像是怪我比较多?”淳于扬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罐药膏递给他:“治伤的,你自己擦。”唐缈盯着药膏和那只骨节分明的手,却不去接。“怎么?”唐缈说:“怕你要求礼尚往来。你不交出钥匙,我可不能给你蛊毒解药。”淳于扬摇头叹气,将药膏塞到他手上:“当我和你一样傻么?我看你也就能……”他锋利的眼神扫向离离,“骗骗她。”离离翘着二郎腿,一直在阴郁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和唐画一样,她的心智也不太健全,却是另外一种不健全。她过于直白。换言之她不懂掩饰,共情心在沉睡,只有欲望浮于表面,所有的道理和逻辑都围绕着欲望野蛮生长,而她的逻辑和欲望直来直去,比如支配她过来的就是对金钱的渴望。她听说唐家有宝贝,所以一路跟踪唐缈来到了风波堡,潜伏在附近寻找机会。为了宝贝,她暗中观察唐家的动静,看到姥姥匆匆跑出谷外后深夜登门。可惜这个纯粹的欲望将她拖入了泥沼,她被看似很好对付的人困住了。直到今天之前,她都没有好好考虑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唐家真的有宝贝吗?万一是讹传怎么办?万一是陷阱怎么办?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换回去一肚子蛊虫该怎么办?那把钥匙……她的眼神里透露出恨意,并且这恨意明显针对的是在场的某个人,可惜无人注意。周纳德还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仿佛心最宽的样子。刚才他就宣布了:“小唐同志你不要危言耸听,我不信!我肚子里长过蛔虫、蛲虫、肝吸虫、血吸虫,就是没长过蛊虫,我感觉你们平时学习文件精神不够,思想都没改造好,又常年处在深山老林不和外界接触,所以才专门搞这些封建迷信!这不好,很不好!”装糊涂的人最难对付,周纳德以退为进,打算固守乡干部身份,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可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语正好相反,离离看见他偷偷地抠喉咙催吐,希望能把蛊呕出来。能呕出来的还叫蛊和毒么?他太低估唐家了。见人都在,唐缈又问:“谁拿了钥匙?”其余人都被他纠缠得无话可说,纷纷以沉默应答。“好吧,”唐缈说,“其实我只有十一粒解药,一天给你们发四粒,到了第三天,你们当中有一位就得做好英年早逝的心理准备了。”周纳德没法继续装睡,坐直了严肃道:“封建糟粕,危言耸听,人民群众的思想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搞混乱的!”唐缈问:“周干部,既然你高风亮节,那么第三天我就不给你解药了,你们家有人为你办后事吗?”周纳德还没来得及说话,离离插嘴:“解药在哪儿?”唐缈冷笑:“藏起来了,怕你们对我下毒手,所以藏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早晚一天杀了你!”离离威胁。“朝不保夕还敢这样说,你也算一条好汉。”突然司徒湖山飞快地跳下天井,躲进客堂,原来乌云兜不住雨滴,噼里啪啦地打了下来,片刻工夫就浇湿了他的衣裳和发髻。老道显得狼狈,不住用袖子擦着脸上的雨水。他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样的瓢泼大雨,会不会稀释外面那圈绿水啊?”好聪明的问题!如果雨水真有稀释毒液的作用,岂不是一场豪雨结束,大家就有逃脱困境的可能了?于是他们顾不得暴雨如注,纷纷冲进雨幕跑向深沟。唐缈脚不方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淳于扬也抓了一把油纸伞跟出去。结果想得太美,绿水接触了冰冷的雨水,顿时沸腾似的剧烈翻滚,液滴飞溅,冒起白烟,简直就像少量水泼进了浓硫酸,初中化学课本就告诉过你这很危险,是绝对禁止的操作。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客堂。“水火无情啊!”司徒湖山感慨,“唐家更是无情,想想当年唐竹仪是怎样对我的,再想想现在的唐碧映、唐缈的恶毒手段,就知道和这家人做亲戚简直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