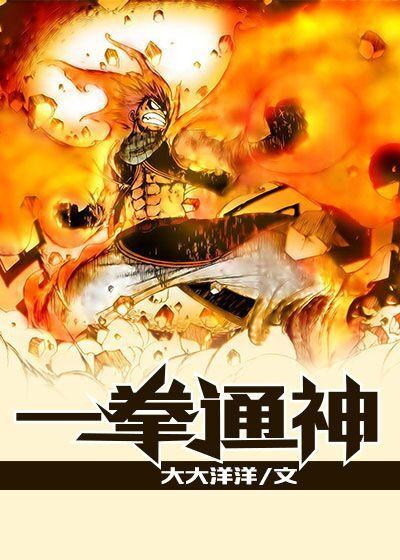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田间欢 宝妻结局解读 > 第108章(第1页)
第108章(第1页)
他突然开口,话语梗涩:“小语,我想了这几天,发生这样的事是我当初考虑不周,不能怪你。”
周语抬眼,她没见过李季这副模样,心痛自责都融在他眼里。
周语像早恋败露又宁死不屈的犟学生,眼里尽是提防,一声不响。
李季朝她招手,“你过来。”
她踌躇,还是走过去。
李季抬起手,周语顿时往后让开。
“……”他惊愕于她的来自生理的排斥,更惊愕于心底扶摇直上的酸味。
李季将她拉近,擦去她嘴角的糖渍,悲悯世人的修眉轻轻蹙着。
他沉吟:“小语,没有下次了。”
下一刻,他突然发力,将她的头压在胸前。
周语喃喃:“……你不怪我?”
李季叹:“亲人哪有隔夜仇。”
那只当年拿过粉笔的手,掌心温暖如旧。她呆在他怀里,不知悸动还是触悟,瑟瑟发抖。
“要真是这样,”她轻声却慎重,“从此往后,我对你亦步亦趋,绝无二心。”
李季手上一顿,下一刻,他爱怜的抚她濡湿的发。
李季走前对她说:“好好睡一觉,凡事有我。”指着茶几上的碗:“汤要喝完,补血的。你看看你现在,没有一点血色。”
说完掩门而去。
周语一觉睡得很沉。
她接连做梦。梦到自己生了只丑巴巴的小秧鸡。她并不嫌弃,倾心抚育。小秧鸡长成凤凰,情意脉脉绕梁三日,阔别远去。
……
再次醒来,天边朝霞绵延。
周语艰难的睁开眼,羽被轻巧,她盖得严严实实。
她感到头痛不适,像害了场大病。
手在床头柜摸到手机,按亮,是下午六点。她这才知道,窗外的红云已是夕照。
余光瞥一眼日历,蓦然大惊,届时离她睡前已过了足足三天!
她乏力,靠在床头。
房间寂寥,尘粒徐徐浮沉。
壁灯亮着,她换下的衣物叠得齐齐整整,搁在一边。拖鞋并排,摆在触地可及的位置。
如泣如诉的小提琴音从窗外传来,宛转悠扬。
那是李季的另一消遣。
一觉睡得太久,她的脑子和视线一样冗长,动起来吃力。
她在初冬的黄昏里凝滞。
她慢慢眨眼,森罗万象一如初始,却分明又有哪里不同。
空,太空了。
不仅房间,身子和心里,都空落落的,空得让人忍不住要含泪祭奠。
周语猛然坐起,抬高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