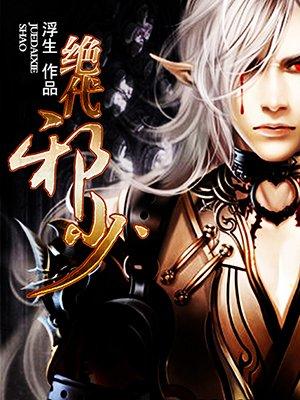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风浅慕衍退婚后我成了权臣心尖宠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江敏突遇意外,一脸受惊地后退,又有几分担心江宏。江蓠却处变不惊,依然是沉静如画的样子,鸦羽似的长睫自然地挺立着,眼神淡淡地看着江宏。
那一身素白衣裳、立于纯白雪地的模样,在一众兵荒马乱中,有一股别样的静美——紧要关头,也无人注意便是了。
惊马持续狂奔到底不妥,江宏一咬牙,一手抓紧车门,放开另一手去拉马缰,他力气不可谓不大,但是却依然止不住奔马。
江宏眼中杀气一盛,松开缰绳与车门,在车辕上一踏,飞身骑到马上,拔下束发的金簪,俯身猛地扎进骏马的脖子。
他一连扎了两次,血液如箭喷到雪地,连绵十几尺,在白雪上面异常刺眼。红樱与江五骇然低叫,江敏也皱紧了眉,眼露嫌弃与恶心。
江蓠也微微拧眉,为这骏马感到可惜。她在山野生活了十多年,与不少飞鸟走兽打过交道,有时候,动物反而比人纯良无害,知恩图报。
惊马终于跄踉着脚步,轰然倒地。江宏已提前下了马,见马终于不动了,长舒一口气,这才转身去看,被摔下马车的江福。
江福抱着自己的右腿惨叫,满头都是冷汗。
第8章展身手
江福在府中效力多年,江宏十分信赖他,大步流星走了过去,问,“你如何了?”
江福依然惨叫着,“啊,我的腿,我的腿!侯爷……”
意识到他的腿多半是摔折了,江宏立即转头吩咐红樱,“去请大夫!”
红樱也顾不得自己的狼狈,连忙去了。
江敏被江福看着长大,江福疼她,她对下人们严苛,对江福却是尊敬的,连忙踱步过去,担忧道,“福伯……”
江蓠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淡然挤开了挡在江福身前碍事的江敏,蹲下身,伸手在江福的断掉的小腿上利落地捏了一番。
江福惨叫声更甚,江敏怒斥,“你做什么!”
江蓠冷淡回应,“看不懂么,我在找断骨的位置,好帮他正骨。”语气并不冲,却让江敏觉得堵得慌。
“大……大姑娘,使不得……使不得……”江福吓得够呛。昨日他在大堂,也听到江蓠说自己会医术,但穷乡僻壤来的女大夫,只怕孤陋寡闻、技艺不精,万一不会接骨,叫他白白受痛呢?万一接骨接歪了,还得打碎重接,岂不是更加凄惨?
江蓠知道江福和江宏此时都并不相信自己,也不多说,只淡淡回应,“父亲放心,必定给他接好。”
她打定主意不对府中人动感情,现下也并非以德报怨,江福也好,江宏也罢,此时在她眼中,都是工具而已。
如果她记得不错,今天的事情做好了,过几日,应该会有一个进宫的机会,来到她面前。进了宫,更方便向前世的仇人讨债。
她说话的的功夫,双手毫不温柔,配合着一动一扭,只听江福一声剧烈的惨叫,断掉的腿骨已然复了位。
江蓠起身,淡淡吩咐,“不要碰他的断腿,将他抬进房间,我要替他施针止痛。江五,去替我拿银针过来,在梳妆台下的抽屉里。”
江五麻利地应声,去了。
江宏见江蓠说话有条不紊,语气充满自信,将信将疑。江福也不知自己骨头接正了没有,见江宏不再反对了,也不敢再说什么,只能口中叫痛,心里叫苦。
几个男丁围过来,小心翼翼地将江福抬入他房间,江宏江敏一起跟了进去。冬日衣服穿得厚,不方便施针,江蓠命人拿剪刀剪开了江福断腿的棉裤裤管。
江宏见她做事细心,有理有据,心里又相信了一层。江敏自然是了解自己父亲的,见江宏神色,便忍不住低骂江蓠,“装模作样!”
江蓠懒得理她,只在心里的账本记下了。她有更大更远的目标,当那个目标达成了,再报复于江敏,事倍功半。
不多时江五到了,手里拿着江蓠的一套银针。江蓠接过,眼神有了温度,爱惜地展开包银针的锦缎,从中抽出细长的一根,扎进江福的腿部穴位。
江福已痛得麻木,心里也是万般绝望,只觉得要在江蓠手中遭罪。然而随着江蓠银针越扎越多,他竟然察觉疼痛正逐渐减轻。
江宏见江福脸上的痛色去了不少,便知道江蓠做对了。
又快又准地扎完十几根银针,江蓠起身,淡淡吩咐,“保持一刻钟,之后取针。拿纸笔来,我开一个消炎止痛的方子。另外,再寻一块平整木板来。”
很快她需要的东西便来了。江蓠执笔写字。江宏挪过去观看,只见宣纸上一个个小字娟秀工整,煞是好看。
江宏老怀甚慰,只觉得自己的女儿甚是知书达理。江敏也在看,她被越英宠坏了,字写得不如何,审美却是有的,当即妒火又多了一分。但眼下没有发作的机会。
江蓠开完方子,恰好红樱带着大夫来了。大夫比不上太医院的大夫,医术却也是不错的。江蓠对同行心存敬意,谦逊地将方子递了过去,请前辈指点一二。
那大夫摸着山羊须,审视着药房,一会儿点头,一会儿疑惑地询问江蓠为何开这味药材,江蓠一一答了。
最后老大夫眼睛越来越亮,喜笑颜开,赞道,“妙啊,妙啊!姑娘当真是后生可畏!”
江蓠淡淡一笑,“老先生谬赞。”
江宏与有荣焉,笑道,“蓠儿不愧是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