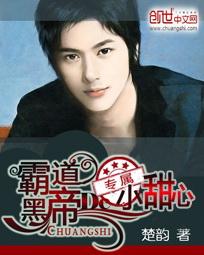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宿醉撒娇 > 第46章 47 春风暗抚(第1页)
第46章 47 春风暗抚(第1页)
()”
事情原比他们想象的快上许多,也不知是天意如此,司夜离带去的密函尚未到达黔郡,那边已经出了事。也不过是瞬息的事,天已变幻莫测,早就风云骤变,风起云涌。黔郡的急报一波一波派人八百里加急送往凤都,怕是朝堂内外早就乱成一团。急报是丑时送达的,西凤帝才刚入寝不多时,殿外的太监就急急忙忙来传报,因着送加急奏折的是御林军统领段晏,徐暮也不敢怠慢,只得呈了奏折上去。此时距离早朝不过两个时辰,西凤帝当下震怒,令徐暮去召了司夜离连夜前往宫中。
在来的路上司夜离得悉了此事,黔郡用赈灾所用银两铸造的堤坝经不起洪水的袭击坍塌,洪水来势凶猛,一路途经几个村庄,淹了数千人不说,害得灾民流离失所。眼看着县令已经无法阻止灾民的群起奋勇,民间对朝廷也是怨声载道,直言西凤帝根本就没有将这笔灾银拨款下去。
司夜离隶属文官,又身为辅相,当属直辖管域吏部,现在这件事出在吏部,和他脱不了关系,西凤帝便是责问,也是拿他先开刀。
他望着浩瀚无垠的无边夜色,眸中幽暗,拢在宽大袖袍中的双手慢慢收紧,多少次他曾这样跌落谷底,眼看着就要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又一次被人推入黑暗。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隐藏在黑暗中的人,无非是想要摧毁西凤帝对他的信任,可越是这样,越说明那个对手在害怕,害怕他的强大,害怕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别人的威胁。
西凤帝端坐在乾清宫的书房中,身上披了件明黄色的长袍,发已束冠。夜色深寒,他却尤似感觉不到。桌案上摆着成沓的各地送来的奏折,有些已批阅的摆放在一边,更多的是尚未看过的。橘黄的琉璃盏中散发着明亮的灯光,殿中仅余徐暮一人在伺候着。
推开厚重古朴的殿门,沿着长长的青石铺成的地砖,那人就坐在案台后,虽然毫无声息的在翻看奏折,殿中唯有层层纸章发出的清脆声。却无端散发出一股令人胆寒的颤巍,和一股肃杀的不安气氛。徐暮见是他,朝他做了个暗示的眼神,那眼神分明是说让他悠着点,皇上正在气头上。
司夜离上前一步,撩起袍服,双膝于地,恭恭敬敬跪下道:“奴才叩见皇上。”他的语声不悲不亢,在这瞭亮的大殿中自成一股特色,低沉中饱含着如沐春风般的清悦,正如他的人一般清逸脱俗,翩然优雅。
西凤帝含眸凝注在案台上龙飞凤舞的字体,一行行一字字皆是对此次辅相疏责的鞭笞声。作为西凤帝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可视作为他的心腹,自然也有人想将其除之后快,又甚者先将他拉下马。怪只怪司夜离风头太甚,又无可找出他的把柄,只好借由此事来扫一扫他的风头。此时墙倒众人推,古往今来都无可厚非。在朝中与他交好之人有之,又有谁敢真的出声去帮他。他心中自当清楚,这件事无非是他圣眷太荣,早就蓄谋已久,否则也不会挑在这个时候。
西凤帝并无让他起来,司夜离也不敢起来。望着高案上神情肃穆的老者,他似乎有些恍然,竟怔然地凝视着他。他知道西凤帝是对自己失望了,因为在那位老者睿智的目光中满含着落寞。或许也不是对他的失望,而是明明知道朝中有着那么一股势力想要去摧毁他安插的棋子,可却无能为力的任人对自己步步逼近。他明明知道是谁,却下不去这个决心除去。为权者,最忌讳的便是优柔寡断。他想要以此来挟制住这股势力,他在等,不知是等一个结局,还是等一个开始。
然而,司夜离也在等。他在等这张黑手浮出水面。对他的打压或许只是一张编织的网,想要网住的是更大的利益。他们没有证据,唯一与这件事有关的便是陈政亦,他自己或许都在迷雾中,被人利用也未可知。
早朝的时候,果然吏部尚书的位置是空着的,据闻陈政亦滥用职权,私自收受好处,已被关进天门府的大牢收押。这件事委实说不过去,若说滥用职权给自己的小舅子还说得过去,这收受好处一说又是如何说起。堂下官员议论纷纷,说是刑部从陈政亦的小妾柳絮那里搜出了不少赃物。柳絮支支吾吾无法辩解清楚,当下也被关进了牢中,而她的表哥也早就携款逃之夭夭,哪怕是一桩冤案,也哪里还说得清。官员们叹息之余,也只叹陈政亦哪里会想到被一直宠爱的小妾给坑害了。
当然,这件事闹得如此之大,也非追究是谁的过错之际。百姓们只知道是朝廷的责任,若说非要找个替罪羔羊也于事无补,当今之计是要如何善后和安抚。事发之初,西凤帝已派人代表朝廷前去,但显然无法昭显朝廷对百姓的重视,以至局面更是僵持不下。官员们终于提议,不诺就让大皇子前去安抚人心,届时再派御林军一同前往押解赈灾的物资。此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耗时巨大,怕是再回来时,大皇子的风头更是无量。现在太子被禁闭,大皇子若是对社稷有功,那只会令他离将来的皇位更近一步。
西凤帝抿唇不语,他的面容被隐在九旒冕之下,十二串玉珠同时将他与大臣隔离开。没有人能揣测得出帝王座上的王者在想些什么,又或者他是想将远在边疆的贤王召回来?大臣们各自揣测着心思,又各自打着算盘,仿佛早就笃定会派大皇子前往。临下朝,大皇子走在前面,不少大臣则跟在后面趋炎附势,言笑晏晏的谈论着无关紧要的事。
司夜离望着志得意满的大皇子凤云殊,黎明的霞光照向万里,而那个人背对着光,光影朦胧间,那一身与生俱来的王者气息淡淡笼于周身,晨风中迎风招展的袍沿猎猎作响,耀金的霞紫如阳光下披着战袍的战士,倨傲的看着他的猎物。他淡淡回眸,春风般轻柔抚过的笑意溢满唇角,那一笑,天地失色。
凤云殊挣脱人潮,朝清冷的他这边走来。司夜离俯身行礼,凤云殊执掌按上他的肩头,笑得意味深长,“司相,其实以你的才华又怎会不懂得审时度势,父皇老了,可你还年轻。”那句话既轻又浅,如流风般随逝,却只有司夜离能听清。凤云殊拍了拍他的肩,将他肩上残碎的落叶扫下。
要想拉拢一个人,要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曾几何时他也学会了这招。只是,他还没到落魄到需要依附他的时候,因为他还不足够跌到最底层。就算是最底层,他也有能力自己爬起来。
出了皇城门,方踏上轿子,他慢慢如雕琢般的笑颜开始一点一点龟裂,当眼底只余下一片狠戾与冷漠时,他缓缓闭上眼。墨色的软轿绣着相府独有的繁复花纹,他屏退随侍的侍女,两个侍女伺候的时日久了也能感觉出气氛的诡异,都战战兢兢退出轿子,轿夫沉默的走着。此时已近辰时,路旁林立的商铺正要早早的开门,看出是相府的轿子都恭敬的避退开。
“流锦。”轿中的男子温言道,他本就受了风寒,寒毒侵体,尚未好全,朝堂事物繁忙,又来回的奔波,声音中满含着疲累。
流锦一柄从不离身的宝剑紧抱在怀中,靠近轿帘,贴着耳朵听轿中人的吩咐。
他用只有两人听到的沙哑声道:“按照计划提前行动吧。”他的话低了下去,声音渐渐消失,良久都只是轿夫抬着轿沿轻微的走动声。
他是累了,劳心劳累到最后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三月三,又为立时的春种,所谓春之祭,也是寓意在一年的春分之际能取个好兆头,望能在这一年中的农作物有丰收,顺风顺水。春之祭于西凤来说本身就是个重要的节日,除了表演、比赛、也是难得的城中闺秀一齐露面的时候,届时也能一览名门公子的风采,场面盛大之余,指不定倒真能有看上眼的。当然,除此外,深受西凤百姓爱戴的宫廷祭司也会前来祝祷。平日里,他们住在皇宫御用的占星殿,凡不得允许,常人难以见到。便是宫中都有繁杂的规格,若非节日,除非祭司推算出什么需要告禀,才会觐见帝王。
西凤是个信奉神灵的国家,祭司相当于国师,在祈祷祝寿等需要神灵护佑的时候,或者打仗推算的时候,都少不了祭司。祭司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深受子民的推崇,连皇室都礼让三分。
祭司又分为最高等级的大祭司,占星师、演算师、推术师等,最小的莫过于巫师,层层等级分明,只唯一一点皆是男子。
祭司院与佛寺的不同之处或许只在于,祭司院乃佛宗的一支,只专供皇室之用,是从佛宗中选出的最有慧根的弟子,分别授予的职业。祭司院为皇室任职已久,历代都有记载,久而久之也就从佛宗中脱离出来,为显区别,已不需要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