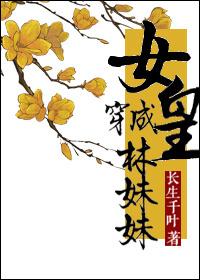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犯罪团伙一般会判几年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这个该死的帽架,该死的帽架,”赖德先生眼泪汪汪地说,“这不像我们美国的,男人们每天晚上都能轻松挂上帽子——每天晚上,先生,您戴着两顶帽子。从没见过一个人戴两顶帽子。一定很管用——防寒。”
“可能我长了两颗脑袋。”汤米郑重其事地说。
“是的,”赖德先生说,“这真奇怪,十分奇怪。我们喝杯鸡尾酒吧,禁酒——不允许,不让我进去。我想我有点醉了——一直不停地喝。鸡尾酒……混合的……天使的吻……是玛格丽特……迷人的尤物,她也喜欢我。马脖子酒,两杯马提尼……三杯‘通往废墟的路’……不是,通往房间的路……把它们倒在一起……倒入一个啤酒罐。我打赌……我说……去死吧,我说——”
汤米打断他。
“好了,”他安慰他说,“现在,回家怎么样?”
“无家可归。”赖德先生悲伤地说,竟抽泣起来。
“你住在哪个旅馆?”汤米问。
“回不了家了,”赖德先生说,“刮尽了我的金钱,吞食一切。都是她干的。白教堂——白色心肝,白头悲死亡——”
但是赖德先生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挺直身体,说话也奇迹般地变流畅了。
“年轻人,我告诉你。玛吉带着我,在她的车里,寻宝。英国的贵族都干这个。在鹅卵石下面。五百镑。不可思议,这真不可思议。我告诉你,年轻人,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心里记得,先生,心里。我们美国人——”
汤米这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你说什么?莱德劳太太用车载着你?”
这个美国人严肃地点点头。
“去白教堂?”还是严肃地点头。
“你在那儿发现了五百镑?”
赖德先生努力地说话:
“她……她发现的,”他纠正他的提问者,“让我到外面,门外,总是让我在外面,这真可悲。外面——总是外面。”
“你还记得到那儿的路吗?”
“我想我记得,汉克·赖德从不会迷失方向——”
汤米二话不说,伸出手拉着他就往前走。他发现自己的车还在原地,然后他们一路向东飞驰而去。凉爽的空气让赖德先生舒服了不少,他不省人事地瘫靠在汤米身边睡着了。等他醒来,头脑清醒,精神奕奕。
“说,伙计,我们在哪儿?”他问道。
“白教堂,”汤米直截了当地说,“这儿是不是今晚你和莱德劳太太来过的地方?”
“看起来眼熟,”赖德承认,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从这儿左拐去了什么地方。就是那儿——那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