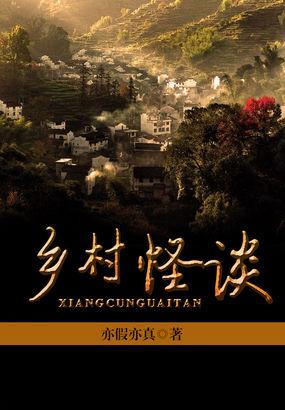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人皮论语和论语密码 > 第43章(第1页)
第43章(第1页)
柳夫人接过竹简,见简上写了一行字,是古字,也认不得。便道:&ldo;我丈夫大概能认得,这竹简能否借用两天?&rdo;
张氏道:&ldo;都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婆婆也去世了,我们留着它有什么用?柳夫人尽管拿去。&rdo;
柳夫人拜谢了,又寒暄几句,留下带来的礼物,告辞回去。
赵王孙找来一把黑羊毛,让硃安世粘在脸上作假胡须,好遮人眼目。
硃安世对着镜子,在颔下抹了胶,捏着羊毛一撮一撮往下巴上粘,费了许多气力,却始终不像,倒累得双臂酸乏,正在恼火,身后忽然传来一串娇腻笑声‐‐是韩嬉,她斜靠在门边,望着硃安世笑个不住。
驩儿的事情,韩嬉始终只字不提,硃安世一直憋着火,却只能小心赔笑,回头看了一眼,嘿嘿笑了两声,继续粘他的胡须。
韩嬉摇摇走到他身边,伸出纤指,轻轻拈住硃安世正在粘的一撮黑羊毛:&ldo;粘斜了,再往右边挪一点儿。&rdo;
硃安世许久没有接近过女子,韩嬉指尖贴在自己手指上,柔嫩冰凉,不由得心里一荡,忙嘿嘿笑了两声,缩回自己的手。
韩嬉笑道:&ldo;粗手笨指的,来,姐姐帮你粘!&rdo;
硃安世只能由她,嘿嘿笑着,伸出下巴,让她替自己粘胡须。
韩嬉左手托住他的下巴,右手拈起羊毛,一缕缕粘在他的颔下,手法轻盈灵巧。
这几年,硃安世终日在征途马厩之间奔波,看的是刀兵黄沙,闻的是草料马粪。这时,脸颊贴着韩嬉的手掌,柔细滑腻,闻着她的体香,清幽如兰,脸上更不时拂过她口中气息,不由得闭起了眼,心醉神迷。
正在沉醉,却听韩嬉轻声道:&ldo;胡茬都已经冒出来了,粘不牢。&rdo;
硃安世睁开眼,韩嬉的脸只离几寸,眉毛弯细,斜斜上挑,一双杏眼,黑白分明,脸上肌肤细滑白嫩。比起妻子郦袖的秀雅端丽,另有一种妩媚风致。硃安世全身一热,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声音异常响。登时窘得满脸通红。幸好韩嬉正专心致志在粘胡须,好像没有听见。
硃安世干咳了两声,才小心道:&ldo;还是我自己粘吧。&rdo;
韩嬉却全神贯注,正在粘一小撮黑羊毛:&ldo;别急,就好了。&rdo;
硃安世只得继续伸着下巴,不敢再看再想,重又闭起眼睛,尽力想着妻子生气时的模样,心里反复告诫自己:郦袖别的事都能容让,这种事可丝毫不容情。
&ldo;哈哈,早知道,我也该剃光胡子!&rdo;耳边忽然传来赵王孙的笑声。
韩嬉猛听到笑声,手一错,一撮羊毛粘斜了,笑着叱道:&ldo;赵胖子,莫吵!&rdo;
硃安世怕赵王孙看出自己的窘状,嘿嘿干笑了两声。
赵王孙笑着走进来:&ldo;不吵不吵,不过下次我连头发也剃掉,你得好好替我粘一粘。&rdo;
韩嬉一边继续粘着,一边笑道:&ldo;你最好连脑袋也割掉,我最爱替人粘脑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