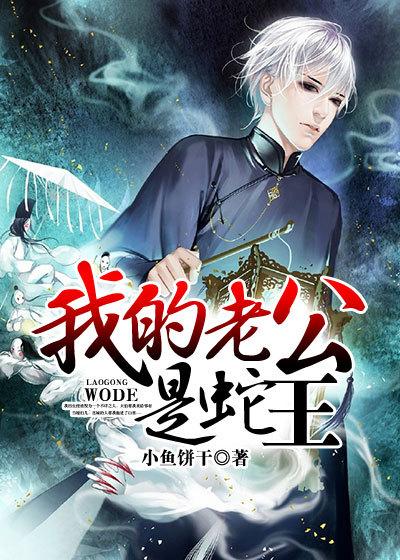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盲狙怎么打 > 第80章(第2页)
第80章(第2页)
彻头彻尾,有的只是利用,再无其他。
至于程珈书的后半生,无论是为先前做过的事赎罪,还是念念不忘地执着在他身上,那都与他无关。
这场游戏,程珈书最早出局。
苏婥发现程控比四年前更可怕了。
有一种莫名的惶恐在她心头发酵。
程控终究不可能亲自带苏婥走。
在这块地上,他不信任苏婥,不信任徐照,等同于不信任与他有关的任何一个人,就不可能不设退路。
男人准备好的车已经停在楼下。
废弃灯塔有前后两道门。
程控提前走的自然是那道隐蔽铁栅后门。
八点准点,程控的车迅速离开。
八点零二分,灯塔前门那块洋洋洒洒地亮起炽色的近光灯,将漫天倾泻的雨水照出逼人的气息。
临海的位置,汹涌的海浪蓄势凶猛地拍打着礁石。
雨势在深夜愈趋瓢泼,洗刷整座灯塔,连原先照明前路的暖灯都在雨水的浸泡中渐变沉黯,一声一息都在透露焦灼和窒息。
祁砚的车最终开进停车场。
然而,等在这的只有苏婥和控制后场的男人,除此之外,就是那段程控早有准备的录音。
开门见山地,男人在眼见祁砚的车熄火后,一把就粗鲁地把苏婥朝未有遮挡的天台上推,以此让祁砚看到他至此都想见的女人。
苏婥的嘴里被男人塞了东西,不仅说不出话,连手上的塑料束绳都在他用劲下束缚得更紧,勒得手腕生生出血。
血渍浸没的痕迹暴露雨下,刺痛的灼烧感随即抽丝剥茧地蔓延在四肢百骸,根本挣脱不开。
祁砚一眼就注意到安稳站着,却被风雨吹得飘摇的苏婥。
他捏着手机的力道加重,撑着的那把黑伞在浓墨泼洒的夜下都无意浸透上渗人的气息,快要和黑衣黑裤的他融为一体。
祁砚的目光起初是带有安抚性给到苏婥的,但在转移向后在男人身上后,滚滚涌动的怒气再没遮掩地扎到他身上,“你想干什么?”
不过三层楼的高度,男人当然听清了祁砚的话。
他俨然气定神闲得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调试着手上那把真猎枪,是他喜欢的刺激大枪,“咔嗒”一声运弹。
苏婥都没来得及换下一口气,男人手上的猎枪枪口就不长眼地正对向祁砚的头,“你猜能登上明天社会新闻版面的,是一个缉毒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意外死亡,还是沂港船舶一把手意外死亡?”
程控的命令,就是让祁砚活着进来,死后再也走不出去。
只他一人出现在灯塔下,车里没人,是信守对话的表现。
但可惜了,没人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