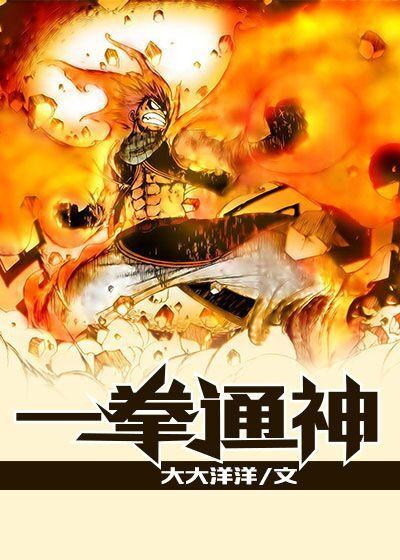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正所谓欲买桂花同载酒 > 第56章(第1页)
第56章(第1页)
秦楚蹙眉,“叫你来是给你们国君治伤的,又不是来认亲的,胡乱叫什么?”
御医去看临江,一脸为难,心道我这是哪句话说错了?
临江无奈,“是宁国公主,你快给国君治伤罢。”
“嗳。”御医起身来,再去给江月白号脉,查看心口的匕首,道:“国君脉象厚重,没有性命之忧,心口的匕首虽然深了些,不过不打紧,并未伤到要害。”
秦楚在心里冷笑,果然是苦肉计,扎的很有分寸。
御医看看临江,嘱咐道:“临大人,我要给君主拔刀,君主失血过多,拔刀之后势必会伤及心脉,还烦劳临大人吩咐,煮上赤豆、红枣、猪肝一锅,待君主醒来即刻吞服,用以养血。”
临江额首,便出去吩咐了。
秦楚坐在那里看着,御医同她揖礼,“臣下要拔刀了,拔刀之痛常人难以忍受,为避免伤及主脉,烦请公主替臣下按住国君。”
为了萌橦的下落,她也就没那么多计较,过来按住江月白的身子,看御医一眼,道:“开始罢。”
御医手法娴熟,迅雷之势就把匕首拔了出来,马上在伤口处撒了止血散。
拔刀的瞬间,溅了秦楚一脸血浆子,倒是江月白,只是疼的蹙了眉头。她想,果然是刀尖舔血一步步走上帝位的,有骨气。
御医给江月白敷上止血散后,便缠了白棉布,叮嘱秦楚,“公主,国君伤在心口,臣下要替国君包伤口,您把国君衣裳褪了,臣下好下手。”
她不大愿意,和御医大眼瞪小眼好半天,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给江月白脱衣裳,只是伤口在胸前,怎么也是避不开,干脆找了把剪刀来,沿着胸口把衣裳剪了。
他皮肤白皙地裸露在她面前,皮肉紧实,是练家子的精壮,平时穿着衣裳看不出,只觉得身形消瘦,但其实脱了衣裳再看,一点也不消瘦,看的她有些心神荡漾。
她脸红起来,心里啐自己,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这样龌龊的心思。
拖着他的背,尽可能让御医包扎的顺畅些,等御医包扎好,她才捋捋江月白的头发,把他放在榻上。
全都处理好,御医才起身道:“臣下去开方子,着药房抓药煎煮,”又从药箱里拿出两瓶药给她,“止血散一日一敷,止疼散一日两敷,劳烦公主莫忘了。”
她接过药瓶颔首,“好,我知道了。”
御医便揖礼,退了。
房中一时寂静,她在床侧坐下来,把药瓶放在床头,撑腮去看江月白。
他的眉头依旧皱在一起,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看着憔悴的很,呼吸也不太平稳,想来胸前的伤口一定很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