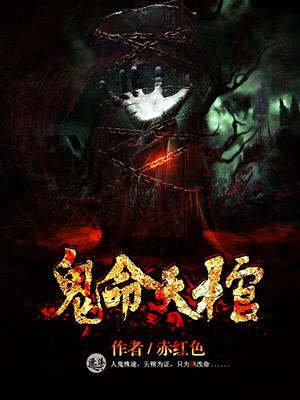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罗曼蒂克消亡史删减视频 > 第23章(第1页)
第23章(第1页)
喝了几大口冰凉的啤酒之后,给第三个&tis;君打了电话。响过不多的几声他就接了电话,他正带儿子逛街买东西,让我等着,他把小孩送回家后便来找我。我说啥事没有,一点不急,你慢慢来。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他迤迤然地晃悠着过来了,穿着雪白的麻制短袖上衣和时髦的球鞋,一条暗绿色的前后侧面满是口袋的质地舒适的短裤。照旧健康略黑的肤色,照旧灿烂地笑着,露出齐整的吸烟的四环素牙齿。
他始终知道怎么穿衣服,怪不得女朋友从不间断,从来不被性困扰。他照旧不爱喝酒,在我的劝说之下仍然坚持要了加满冰块的可乐。我又要过三四次啤酒,并且得意地说,啤酒的好处是可以一直喝下去。他低头望了望自己的空杯子,说,太甜了,一直喝确实吃不消。接着便要了冰冻的柠檬茶。
闷热的天气逐渐变得凉爽,我们一直消磨到六点。我约了第二个&tis;君的太太去他们开的餐厅晚餐,他便又陪我走去襄阳路靠近淮海路的地方。时间尚早,我们绕了一个小路口,以便能路过汾阳路,在路口稍作停留。
这里一点都没变,转眼十几二十年了。我想起我们和第二个&tis;君在这附近共同度过的时日,再一次提议他跟我一起去吃晚饭。他大概是说家里已经准备了而且他想回去陪儿子吃饭之类的话再次推脱掉了。我们便在餐厅所在的马路对面非常随意地挥手告别,他继续向前朝淮海路方向,我则横过马路走进弄堂,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已是所谓诀别的现实。
事后我常常后悔,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晚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然这毫无意义。晚餐之后我坐车到曾经长年厮混的体育馆边上,在陈年得仿佛一直就存在的华亭宾馆幽暗的大堂酒吧里与最终在电影里出演了王妈的女演员碰面。
我坐在角落里,看她戴着一个大大的有着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却仍然吃力地摸索寻觅而来。我一直向她招手,然而她视而不见,这使我怀疑她有一千度左右的近视,但从没跟她确认过。她不施脂粉,放松随和,经常爽朗地大笑,魅力自成一格。
事后发现,到了镜头前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表演又或者一切都无法表演,有魅力的在镜头前仍然有魅力,平庸的在镜头前仍然平庸,乏味而一脸杂念的在镜头前仍然乏味而一脸杂念。
第二天我便回北京,之后因为工作和他在两三个月里通过数次电话,我当时希望他能到北京来,而他不想远离家庭或是手头正准备别的工作。他似乎不想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总之没有成功。
之后在2015年年初我们又通过几次无关痛痒的电话,他当时热衷于跑步,每晚八九点钟在小区的院子里奔跑。有一两次好像是我打给他,他没有接,事后回过电话来说跑步去了哈哈之类的。
一个多月之后的四月一日,我照旧一大早就跑到剪接室里枯坐,打发着眼下每一天千篇一律的沉闷的工作时间。上午十点钟得到消息,当天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第三个&tis;君趁着太太去买菜的时机自杀,成功身亡。我便给上海的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回答说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从家里跳楼死的。
挂了电话,我感到惶恐委屈。怎么会感到委屈?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不发一言地坐在原地。十几分钟后,刚才的朋友又打了电话回来急切地纠正,说,不是跳楼,不是跳楼,是在卧室里吊死的。嗯嗯,这样要好得多了,我对着电话说。不管怎样,我感到这样确实要好得多了。所谓生者的无谓的羁绊。
这也使我常常会想,事实上我们并不像关爱自己的脆弱般真正关爱死者。
初见第三个&tis;君是在1996年9月,他风风火火地来,用硕大的拉杆箱撞开门,把自己的首次登场安排在门与拉杆箱的后面,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不知是否经过排练。他瘦黑的脸有一多半被蛤蟆镜遮住,上面加盖了一顶雪白的棒球帽,豁着一嘴疑似四环素的吸烟的牙齿笑着。
他大大咧咧地进来,身后还带着梗,尾巴似的z小姐自此出现了。不过她要低调得多,友善地跟每个人点头微笑。z小姐长得还算精致,是那种比较贴心的充满家常味道的好看,身材普通。她在由某个综合大学挂牌的疑点重重的野鸡表演学院里学习所谓表演艺术,学制一年。而他则在看上去不那么野鸡的电影学校表演系的表演训练班学习所谓表演艺术,学制也是一年。
z小姐班上一屋子的美女,在和他变得熟络之后,我间或去过两到三次,并没有得到什么,后来就不去了。&tis;君却一刻也不得闲,时至今日我只能将他一直旺盛的桃花归结于他身上那一大片醒目的粉红色胎记,从后背一直蔓延到屁股和腹部。此外大概还因为他善良正直。
只在认识的两周后,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谈话就是围绕着他骤然绽放的桃花展开的。当时我正在宿舍五楼的楼道口抽烟,假装深沉地凝视黑夜,其实不过是寂寞难耐,日子难熬。他从楼下上来,站到我身边,也点上一支烟。我瞟了他一眼,懒得理他,扭头继续假装深沉,凝视黑夜。
来劲,真他妈来劲。他嘴里念念有词,独自激动着。我转过头瞪他,你他妈有病啊。他便立刻将身体凑了过来,跟我讲述他今夜的美好奇遇。
我刚才不是去上夜自习了吗?
你个表训班的上什么夜自习嘛?
大家聊天嘛,多接触嘛,解放天性啊,老师交代的啊。
训练完解放天性,同班的一个江西女孩特意绕过好几张桌子走过去问他,你想不想打扑克?去哪里打?去我家,我跟那个谁‐‐是他们班另一个女孩‐‐合租了房子住,很近,走路十分钟。好啊,那玩玩吧。他便跟在她身后,在学校后面光线昏暗的小路上前行,偶尔安静地说上一两句话,轻言慢语,像是突然都变成了庄重的人。
女孩租住的是那种老式的五六层高不配电梯的板楼,他们一前一后上楼梯,能听到脚步声在此时安静的楼梯间里回响,便不约而同地调整步伐,使步调完全一致。她在中间故意变调了几次,他也都迅速跟上。
她在某一级楼梯上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一下,他撞了上去。她是故意停下的吗?他想。他是故意没有停下的吗?她想。虽然只是轻轻的碰触,但四下无人时的身体接触免不了意味深长,引人遐想。
她继续上楼,他感到机不可失。他伸手去扶她的腰,最先只是似有若无的碰触,之后两只手都上去,扶在她腰上。她的腰不算纤细,但富于肉感,十分柔软。她没有做出回应,仍然沉默地拾级而上。他心领神会,知道一切皆被应允,便将手移到她的臀部,随着她迈上台阶。
他感到她的臀部在手心滚动,能逐渐察觉她步伐的困扰与波动。她的脚步透露出苦恼,仿佛在忍耐什么,等到恰到好处时,他将手准确无误地放到她双腿中间,她停了下来。他们去了顶层通向平台的夜里不会有人经过不易被察觉的楼梯间的拐角。
他说她激情四溢,大胆豪放,百无禁忌,他说自己表现一流,算得上神勇。我唯有勃然大怒,畜生啊,你们丫的。他哈哈大笑,得意又幸福地望着窗外。然后呢?我仍然追问。然后就下楼跟她同屋打扑克去了,她给我弄了个水果拼盘,牛奶、酸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