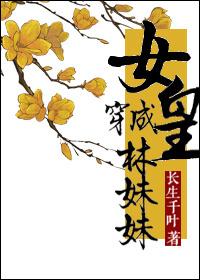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独行女孩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ldo;让我来吧!&rdo;
我把箱盖打开后,他急忙走上前来。我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单膝跪在地上。托尼俯下身子。两只手抓住箱子里的一些内衣,把它们往身后扔。他的样子真可笑‐‐就像一只活泼的小狗为了寻找地下的老鼠正在挖地洞一样。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继续说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能平复情绪,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行。&ldo;如果我知道这些东西这么快就会被弄乱,当初就不用精心打包了。&rdo;我依然看着他,我的手却偷偷地在身后的地板上摸索着。我没有搞错方向吧?应该在那儿吗?我能活命就指望它了……我继续说:&ldo;小心我的薄丝纱礼服……那可是一
件珍贵的晚礼服……&rdo;
&ldo;你可以再买一件‐‐用鲁伯特的那些钱。&rdo;托尼没有再说话,我能听到他刺耳而低沉的喘气声。他的脸和眼睛已经发红了,他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他会把钱分给我?他会让我活着吗?
一面镶着银手柄的镜子放在质地软的东西中间不容易碎掉,现在,它掉在地上摔碎了。
&ldo;不要打破玻璃,会带来霉运的。&rdo;我依然试着和他交谈。我把右胳膊伸向身后尽可能伸到的距离。最后,我的指尖碰到一个光滑、冰冷的东西。我小心地抬起胳膊,回过臂弯,用腰的力量支撑着手臂越抬越高,越过了托尼的肩膀。如果他这么快就把头转过来……
箱子底部的一条长长的衬裙被他扬起手扔在了身后。他的双手在余下的几件小东西中间贪婪地寻找着‐‐箱子里还剩一瓶雪花膏、一叠手绢、一套装在蓝色皮盒子里的美甲用具。突然,他的手停住了……
&ldo;你这个魔鬼!没在这儿!&rdo;
他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刹那间,他眼中的惊讶变成了怀疑。刹那间,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击中了他双眼之间的位置。制门器打在了他的额头上,紫色、绿色、白色和金色在灯光下反着光。制门器当啷一声掉在地板上,上面粘着黑红色的血迹。托尼脸朝下倒了下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把他翻转过来。他被打晕了,现在的他好像又变回了原来的托尼‐‐一张年轻细嫩的脸,朴实、善良。
血已经开始凝固了。我摸了摸他的动脉,如果他一会儿醒过来怎么办?到时候我怎么办?
我在两分钟内穿好了衣服。把所有东西,包括钱、手表和其他我放在走廊桌上的小东西胡乱地扔在箱子里。我拎着箱子跑下了楼梯。我很快打开了前门。我站在房子外面,关好了大门,里面的弹簧锁锁好了。此时的街道沉浸在灰暗的黎明里。
我把箱子放在路边,然后来到隔壁俱乐部会所的门前。我把手指放在门铃上一直按下去。
三分钟以后门才打开。一个穿着睡袍和拖鞋的老人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我手里拿着一张五美元纸币和一张名片。我说话的语速很快:&ldo;很抱歉这么早打扰您。有个装抵押文件的包裹从隔壁的窗子掉在您的花园里了。如果您现在找到包裹并把它交给我的话,这五美元就是您的了。包装纸是粉红色的,包裹大约六英寸宽、八英寸长,上面贴了邮票,是寄给我的。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rdo;
&ldo;好的,小姐。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rdo;
他关上了房门。我焦急地等待着。托尼趁我站在隔壁房门外的时候醒过来怎么办?门又打开了,我松了口气。老人手里正拿着我的包裹。
&ldo;给你,小姐。&rdo;
&ldo;谢谢。&rdo;我把五美元递给了他。我把包裹放进箱子,然后抄近道来到第五大道。
我很幸运。半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有辆出租车刚刚停在路边。两个穿着晚礼服的年轻男人和一个身着银锦缎的女人晃晃悠悠地走下车。一个男人扶着那个女人进了公寓楼。另一个男人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
我打开车门,开始往里面提箱子。&ldo;让我来吧!&rdo;这个喝醉的年轻人有些飘飘然了,不过很友好。
&ldo;听着,女士,&rdo;司机越过他的肩膀和我说,&ldo;他们是我今晚最后的乘客。车里的油剩得不多了,而且,我想去吃早饭,所以,我现在要回车库。您得另外找辆出租车。&rdo;
&ldo;在这个时问我找不到其他出租车,如果找不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rdo;当然,这不是真的。我必须赶在托尼醒过来之前离开这里,&ldo;请送我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俄亥俄公交终点站。&rdo;
&ldo;你不能拒绝一位女士:,&rdo;年轻人借着酒劲勇敢地说,&ldo;绅士从不这么做。&rdo;
他终于打开了计价器:&ldo;我不是绅士,不过,我们正好顺路。&rdo;
我靠在人造革的座椅上,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一夜没合眼了。
在这个时间,第五大道上没什么车辆和行人。司机在街角处放慢了速度,但没有停下来等红灯。薄雾从港口的方向飘过来。房子、公园和天空与车轮下的柏油马路一样呈现出灰白色。
行至五十九街的时候,一道银光穿透了所有的灰暗。薄雾之上,太阳正慢慢升起。到了五十七街,路上已经有开去附近餐馆的牛奶车和面包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子在四十九街转向东边,接着又向南开往麦迪逊大街。